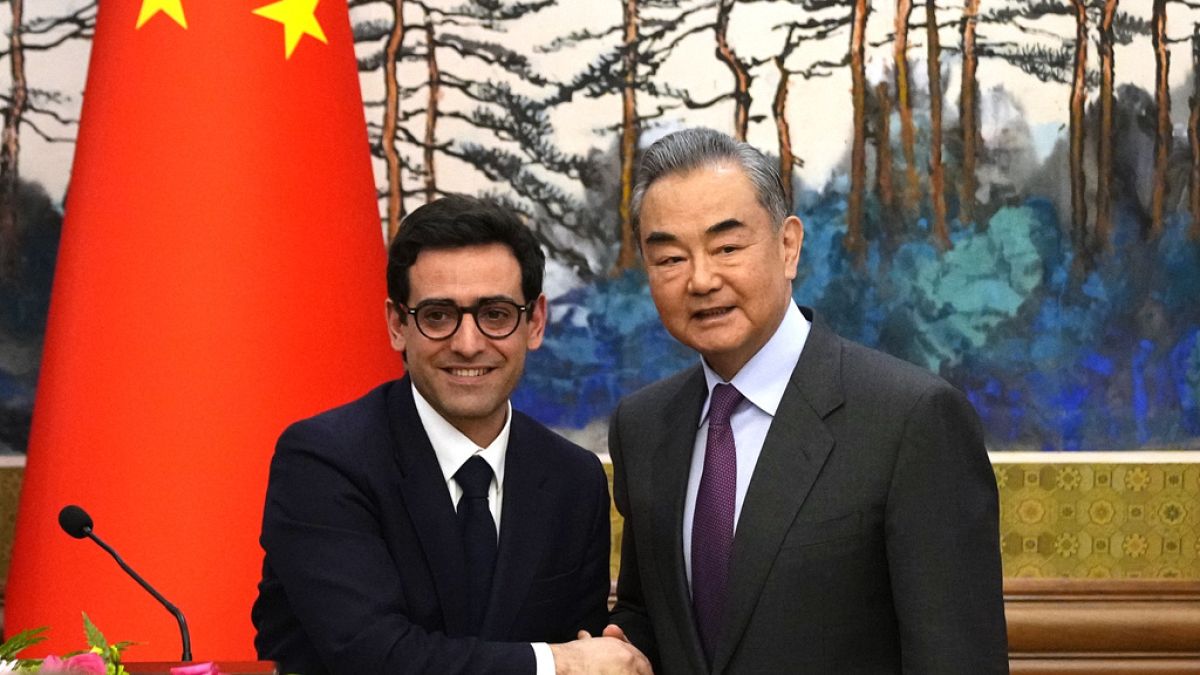當歐盟委員會主席烏蘇拉·馮德萊恩準備向她的新學院分配職務時,沒有人想到斯洛維尼亞會把她拖入一場涉及共產主義時代間諜指控的國內糾紛。
馮德萊恩的政黨原定於本週舉行,這個擁有約210 萬人口的阿爾卑斯山小國在最後一刻更換委員提名人選後,瑪爾塔·科斯獲得了盧布爾雅那政府的認可,這使得馮德萊恩的政黨崩潰。
總理羅伯特·戈洛布領導的自由聯盟立即因此舉而受到批評,右翼民粹主義 SDS 批評科斯缺乏經驗,並涉嫌參與前南斯拉夫特勤局 UDBA。
“你能想像,例如在德國,有人會提名一位背負著過去斯塔西同事身份的候選人嗎?” SDS 歐洲議會議員羅馬納·托姆克 (Romana Tomc) 告訴歐洲新聞台,他指的是臭名昭著的前東德特勤局。
“這對我們來說是不行的,”她補充道。
雖然科斯駁斥了這些指控給歐洲新聞台的聲明這些指控在布魯塞爾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因為斯洛維尼亞是否無意或以其他方式將一名前間諜任命為歐盟最高職位。
但科斯的南斯拉夫特工機構過去意味著什麼?
UDBA 有何故事?
戰後西巴爾幹社會南斯拉夫政策的批評者經常指出 UDBA 運作的極端例子,包括法外謀殺,作為前政權壓迫和嗜血本性的標誌。
然而,根據克羅埃西亞歷史學家 Hrvoje Klasić 的說法,與當時世界各地的其他安全機構相比,UDBA 及其 1960 年代後的改革方案 SDB/SDS/SDV 很少有什麼與眾不同。
克拉西奇告訴歐洲新聞台:“在南斯拉夫解體後的國家中,政治右翼人士中與南斯拉夫有關的一切都被視為先驗的負面因素。”
他補充說,與其他更惡毒的特勤部門進行比較並不能描繪出全貌。
“你不能將 UDBA 與羅馬尼亞安全局、捷克斯洛伐克特勤局 (StB/ŠtB) 或斯塔西進行比較。”
「將史塔西與它進行比較就像將東德與南斯拉夫進行比較。雖然南斯拉夫實行共產主義並由一黨統治,但與東德相比,南斯拉夫是一個更自由的社會,」克拉西奇說。
兩國有著完全不同的發展軌跡。與二戰後蘇聯佔領德國東部領土而發展的東德不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是獨立治理的。
這帶來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問題:隨著冷戰緊張局勢加劇,貝爾格萊德兩個壓力越來越大、有時甚至充滿敵意的團體之間的空間不斷縮小,加劇了人們對民族主義僑民煽動暴力、敵意接管或全面入侵的擔憂。
雖然完全屬於蘇聯集團的東德使用一切可用手段讓居住在那裡的人們服從並遵守規則,但南斯拉夫將目光投向了那些可能試圖從國外破壞其體系的人。
反過來,國家安全機構負責人亞歷山大·蘭科維奇則加強了對國家安全機構的控制。
UDBA 針對那些最強硬派的秘密行動——例如納粹合作者和烏斯塔沙指揮官博日達爾·卡夫蘭(Božidar Kavran),他在策劃起義時被捕並隨後被絞死——被用來作為一種非常公開的威懾,並提醒人們誰是負責人。
“可口可樂共產主義”和豺狼卡洛斯
然而,蘭科維奇的個人不滿引發了政治迫害,促使人們需要砍掉他的職位,並確保南斯拉夫眾多民族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再掌權。
「UDBA 的工作存在許多違規行為,但必須指出的是,在1966 年,正是由於這些問題和大量虐待案件,特別是在科索沃,其最高負責人,或當時被稱為“南斯拉夫第一警察”的蘭科維奇被解雇了,」克拉西奇解釋道。
UDBA 2.0——現在被稱為國家安全局,塞爾維亞語中的SDB,克羅地亞語中的SDS 和斯洛維尼亞語中的SDV——變得去中心化,南斯拉夫六個共和國中的每一個都控制著自己的分支機構。
20 世紀60 年代的轉變發生在這個國家,由於擔心與冷戰分歧中的任何一方過於友好,慢慢地擁護了被稱為“可口可樂共產主義”的東西——它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品牌,充滿了開放的態度。
當南斯拉夫公民熱衷於週末去義大利旅行、穿著藍色牛仔褲和阿迪達斯運動鞋時,在全球安全領域,南斯拉夫人決定不再只是兩位參與者。
安全機構與從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到伊利奇·拉米雷斯·桑切斯(又名“豺狼卡洛斯”)等主要恐怖分子的所有人都有合作。的積極作用,摩薩德將其列入通緝名單。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豺狼被聘為 1984 年薩拉熱窩冬季奧運會的安全顧問。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UDBA 甚至可能透過與左翼紅色旅的接觸,在鄰國義大利的「領導之年」(從 196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末的政治暴力和社會動亂時期)中發揮了作用。
同時,對民族主義僑民和流亡納粹高層合作者的一系列血腥域外處決——例如納粹德國衛星國家NDH在西班牙負責二戰集中營的最高人物馬克斯·盧布里奇(Max Luburić)——被棍棒打死——UDBA身上全是指紋。
「冷戰期間每個國家都設有秘密機構,其任務是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保護國家。中央情報局、軍情五處等機構也使用許多不可接受的手段來保護本國的憲法秩序。
「然而,社會的自由和民主程度越高,這些機構的角色就越不重要,」克拉西奇解釋。
無論如何,您如何知道誰為 UDBA 工作?
科斯在這一切中扮演什麼角色?克拉西奇解釋說,UDBA 的工作方式使得很難確定誰是真正的特工,誰是可能因良性問題接受採訪的普通公民。
此外,UDBA 將其邀請進行對話的所有感興趣的人歸類為“線人”,包括科學家、記者或外交官。
「它是這樣運作的:如果你是物理學教授,你去美國或法國參加核物理學家國際研討會,他們會在你回來後與你交談,詢問是否有提到核武或諸如此類的事情。 」
“然後你會重述發生的事情,因為這對國家和你作為科學家所看到的事情感興趣,有人會記下這些信息,作為某某教授的信息。”
克拉西奇說,到 2024 年,這很容易被操縱,將該人描繪成前特工人員。就科斯而言,這與對歐洲或其安全的任何擔憂沒有什麼關係,尤其是當它涉及到一個在南斯拉夫及其特工機構不復存在時已經20多歲的人時。
「這在國內爭吵和國內政治鬥爭中很常見。給某人貼上這樣的標籤並不一定意味著警告歐洲有危險人物將擔任其職務之一。它更適合用來抹黑一個人或其政黨,所以他們在下次選舉中獲得的選票會減少,」他解釋道。
但這種類型的淨化——質疑和罷免與過去可能受到污染的政治政權有關的公職人員——在前南斯拉夫的例子中被證明是不可能的。
他解釋說,“在克羅埃西亞,有很多人作為警察為部隊工作或作為安全機構的一部分,然後積極參與保衛國家”,在1991年至1995年獨立戰爭期間。
“那麼你崇拜誰呢?1985年竊聽克羅埃西亞極右翼移民電話、1991年在前線受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