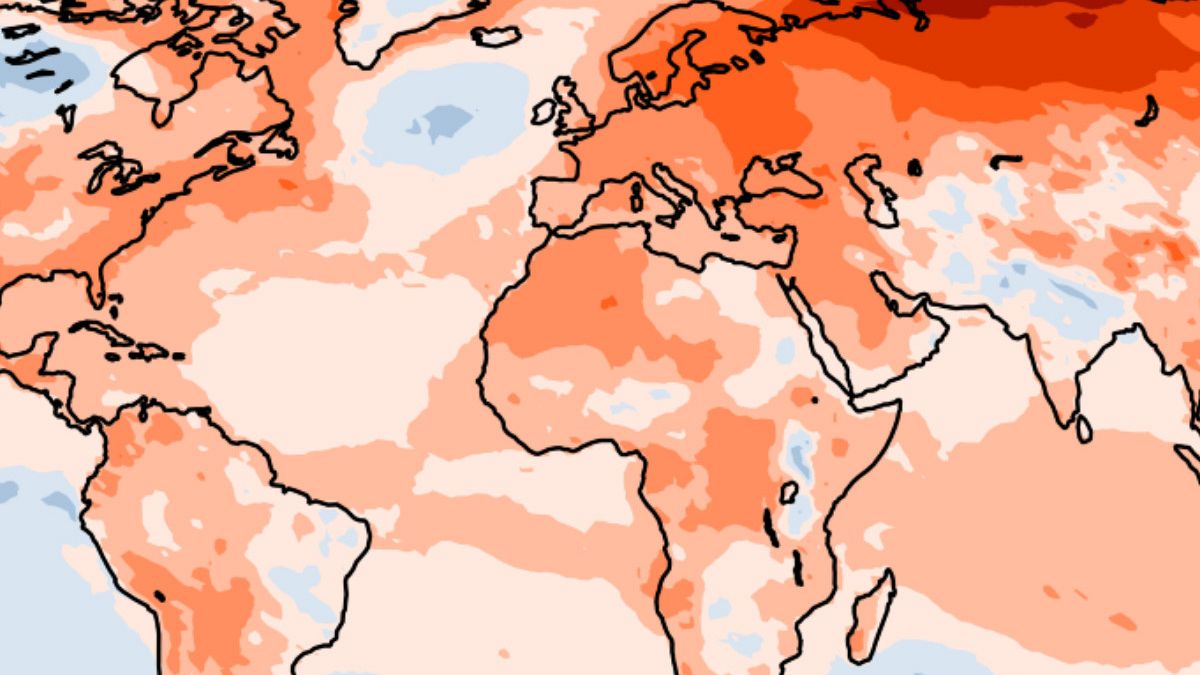一段時間以來,瑞士女性政治家一直在處理議會內的騷擾問題,但她們在網路上受到的辱罵影響了她們的個人生活。
一個2016年網路活動發現瑞士議會中的許多女性每天都會在工作場所遭遇性別歧視和騷擾。但在這個數位時代,瑞士女性政治家也成為辦公室外網路霸凌和辱罵的受害者。他們中的許多人表示,在談論某個問題或發表意見後,他們在社群媒體頁面上發現了有關其出身、觀點和性別的不當評論。
“人們認為我在強姦案上撒了謊”
盧塞恩附近的楚格州前議員約蘭達·斯皮斯-赫格林 (Jolanda Spiess-Hegglin) 表示,當她開始成為社交媒體上網路霸凌的目標時,她感到「無助」。
2017年12月,這位綠黨成員對另一名瑞士男性政治家提出強姦指控後,發現自己捲入了一場政治醜聞。
「人們認為我在強姦指控上撒了謊,因為醫院無法證明使用了藥物,這引發了一場令人討厭的媒體迫害,我成為所有瑞士小報的受害者,」她告訴歐洲新聞。
即使事件已成為過去,這位前瑞士政治家表示,她仍然在社交媒體和電子郵件上收到惡意評論。
但斯皮斯-赫格林並不孤單。另外兩位瑞士女政治家向歐洲新聞台講述了她們的政治生涯如何讓她們遭受言語騷擾。
“我感到憤怒和害怕”
日內瓦州市議員兼代理代表阿曼達·加維蘭內斯 (Amanda Gavilanes) 表示,她在處理言語辱罵方面經歷了艱難時期。
「我第一次經歷辱罵是在2013 年接受電視採訪之後,當時我為當時工作的反軍國主義遊說團體進行了辯護。我收到了一封寫得很糟糕的信,其中侮辱了我和我的家人——而且那是相當困難的。
加維拉內斯說,這封信讓她徹底崩潰,她花了大約兩個月的時間擺脫這一切,因為她感到非常「憤怒和害怕」。
“我的同事告訴我不要理睬它,我就這麼做了。我開始忽略之後受到的所有侮辱,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處理這種情況。這非常暴力。”
2017 年,她接受電視採訪,為在公共游泳池穿布基尼的女性辯護,之後,她的 Facebook 頁面上出現了大量網絡騷擾,她被稱為“妓女”和“婊子”。
這位市議員表示,她現在後悔沒有從一開始就對網路騷擾提出投訴,直到她突然採取行動。
“我最終提出了投訴,投訴的暴力程度比我之前經歷的要少。”
對加維拉內斯來說,由於表達自己的觀點或作為一名從政女性的事實而不斷受到辱罵,這讓她重新考慮是否想繼續擔任公職。
「最糟糕的是,人們總是挑戰你的觀點,告訴你你錯了。當人們做出不同的反應時,你會問自己為什麼要從事政治工作,為什麼要捍衛男女平等的權利。性別歧視的方式或侮辱你。
加維拉內斯認為,瑞士的政治制度是對女性政治家進行謾罵的催化劑,因為它「剝奪了女性在極其男性化的環境中為政治體系帶來的專業知識的資格」。
加維拉內斯在談到瑞士政治內部對女性的言語辱罵時表示:「(瑞士)政治中存在著一種對暴力的接受形式——一種結構性性別歧視——因此對女性政治家的言語騷擾與男性政治家所受到的不同。
“我很遺憾言語虐待改變了我的行為”
另一位自稱遭到辱罵的瑞士政治家艾達·馬拉 (Ada Marra) 表示,她感覺自己「可以自由地接受社群媒體上的侮辱」。
對瑞士國家議員馬拉來說,言語騷擾事件尤其引人注目。這件事發生在大約一年前,當時馬拉在瑞士國慶日寫了一篇關於瑞士認同政治的文章。
她寫道:「一個瑞士的想法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他們有著不同的想法和意見,以及不同的優先事項和問題……我的瑞士不是你的,你的瑞士也不是我的。
但令她沒想到的是,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反彈,網上有人炮轟她是“妓女”、“愚蠢的移民”,並“交出瑞士護照去意大利”。
馬拉堅稱,這些侮辱源自於她談論移民和融合等煽動性議題。
“當你談論這類話題並且你是一位有移民背景的女性時,反應會非常激烈。”
和加維拉內斯一樣,馬拉也對沒有及時提出投訴感到遺憾。
“我消化這些侮辱太久了,所以現在我決定係統地對一切提出投訴。”
但這位副警長最遺憾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網路上的謾罵改變了她對某些事情的行為:「我現在只要打開郵箱就會感到焦慮。我花了好幾年才意識到我對某些事情變得偏執。
據馬拉說,針對她的主要是極右網絡和政黨的成員。但她表示,他們的侮辱不會阻止她表達自己的觀點並追求她的政治生涯。
瑞士關於言語騷擾的法律是什麼?
簡而言之:根據日內瓦律師帕斯卡·里茨的說法,這取決於情況。
「這取決於你如何定義言語騷擾,」他對歐洲新聞說。 “在瑞士法律中,我們沒有與騷擾相對應的具體刑事犯罪。”
但是,裡茨說,在騷擾者的行為中,有幾種可能的刑事犯罪行為。
一切涉及損害某人名譽的行為,例如誹謗、誹謗或侮辱,都可能屬於刑事犯罪,受害者可以提出投訴。
他補充說,因此,要提出網路霸凌投訴,必須從刑事角度以「損害某人的名譽」為由提出投訴。
同一行為可能犯下的具體罪行需要出現在投訴中。
例如,如果有人透過即時訊息侮辱或誹謗他人,則可以提出誹謗和濫用電信的投訴。
投訴應提交給警方或檢察官辦公室,並且需要在事件發生後的前三個月內發送。里茨說,唯一的例外是脅迫,它的時效比其他犯罪更長。
如果檢察官在審判過程中得出結論認為事實構成刑事犯罪,那麼他們可以自由下達定罪令。
里茨說,制裁措施從罰款到監禁不等,根據騷擾者的行為和過去的歷史,也可能是緩刑。
人們如何看待這個系統? 「有人說處罰力道不大,也有人認為這個制度主要是為了社會安寧,」該律師說。
婦女們的反擊
由於受到了所有言語騷擾,斯皮斯-赫格林決定親自處理此事,反擊網路霸凌行為。她創立了#NetzCourage,這是一個非政府組織,為面臨網路辱罵和仇恨言論的女性提供支持。
該組織不僅為受害者提供法律建議,還試圖與網路霸凌者展開對話,以使他們更加意識到自己造成的傷害。
#NetzCourage 特別適合在公共領域工作的女性,無論是政治家、作家還是活動家,因為她們是最容易遭受網路霸凌的群體,該組織網站稱。
「自 2016 年 #NetzCourage 成立以來,受到網路言語騷擾影響的人們不再孤單。我們支持受害者應對並幫助他們迅速重新站起來。我們透過與受害者對話,成功減少了仇恨言論。肇事者,」她說。
兩年來,該組織的創始人提出了大約 180 起投訴。
Gavilanes 和 Marra 都認為 #NetzCourage 等組織的工作在瑞士至關重要,但兩人都同意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教育年輕人了解網路言語騷擾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