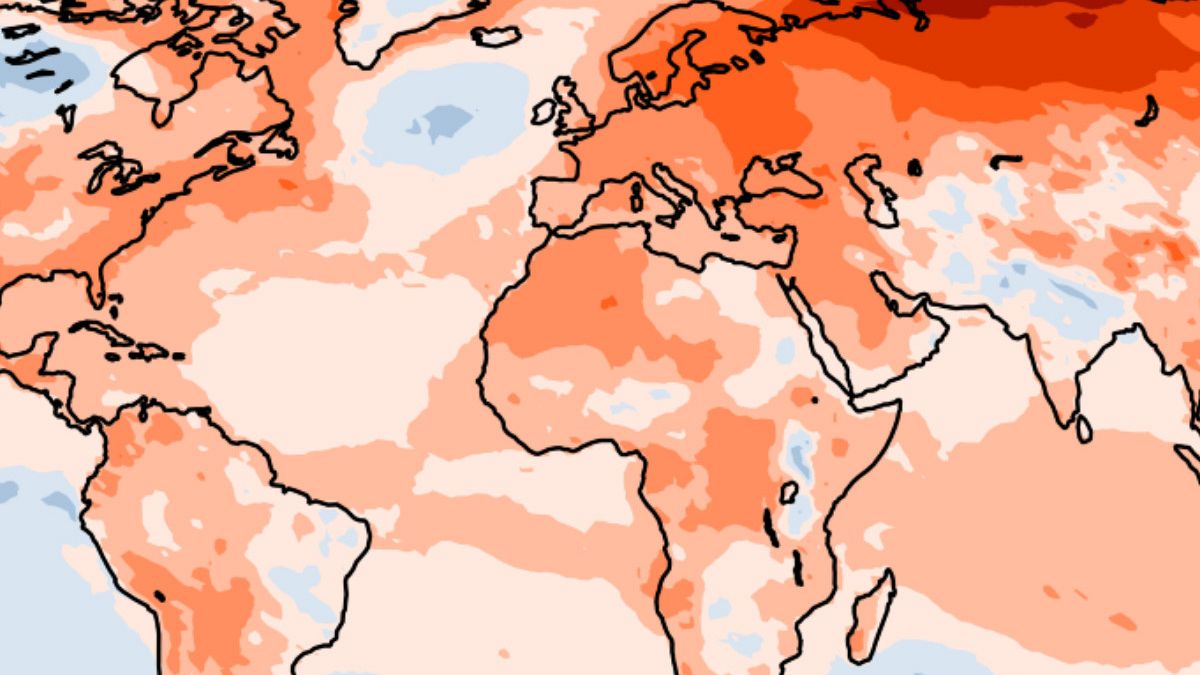2016年,來自馬德里的記者何塞·努涅斯(José Núñez)在位於希臘西北部約阿尼納市外六公里處的卡齊卡斯小鎮的一個由軍方管理的難民營裡度過了40天。
該網站成立於 2016 年 3 月 17 日,收容了數百個移民家庭,主要來自敘利亞、阿富汗和伊拉克。
在那裡期間,努涅斯了解了許多流離失所者的心碎故事,並經歷了營地內惡劣的生活條件。
雖然他從未打算寫一本書,但回到馬德里後,努涅斯開始寫下他在難民營期間能回憶起的一切,他稱這對他來說是一種「宣洩」。
六年過去了,他現在出版了《Shukran 我的朋友》,這本書記錄了他在卡齊卡斯的經歷,並分享了他遇到的難民的許多個人經歷。
這本書獲得了西班牙最負盛名的文學獎之一的Círculo Rojo 獎的提名,也突出了營地中許多志工所做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工作,努涅斯將他們稱為這本書的「英雄」。
歐洲新聞文化頻道採訪了努涅斯,更多地了解他在卡齊卡斯的經歷以及他認為寫這本書的重要性。
歐洲新聞文化:是什麼啟發你寫這本書的?
何塞·努涅斯:在難民營的日子裡,有些事情讓我想:“我應該寫這個。”後來,當我回到正常生活後,我很難回憶起在卡西卡斯的日子,我開始寫作作為一種宣洩。所以我想這是我個人的需要和我想讓人們、我身邊的人知道我在那裡經歷過的事情的結合。最後變成了這本小書。
您如何描述您在營地期間的生活?
我想最能形容它的詞是「絕望」。當然,在日常生活中這也是艱難的、不公平的、困難的……但就我個人而言,我想說的是,我感受到的最多的感覺是絕望。它不僅生活在這樣的條件下,而且你不知道它會持續多久。你得到歐洲關於截止日期和目的地的承諾,但時間流逝,一切都保持不變。這是絕望的,但奇怪的是,希望從未失去。
希臘一直面臨著改善設施和移民處理的巨大壓力。成功了嗎?
2016 年,當我在那裡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沒有拖車之類的東西,只有帳篷,根本不防水,所以下雨的時候就是一場災難。地板是石頭舖的,食物是由獨立志工提供的……從我看來,負責運作的組織的工作還有很多不足之處。如果沒有獨立志願者,我不知道那些人會怎麼樣。當然,情況有所改善,但在那些日子裡,你為自己是歐洲人感到羞恥。
關於他們離開祖國的原因,營地裡的人與你分享了哪些故事?
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原籍國。有些人是為了躲避阿薩德的炸彈,有些人是為了躲避伊斯蘭國……他們會向你展示他們的家園被拆成廢墟的影片。有些孩子可能會非常直白,當他們告訴你他們的國家時,他們會做出砍掉自己頭的手勢。有些人告訴你一切都是為了宣洩,有些人則寧願不記得任何事情,只是為了向前看。我記得一位難民婦女如何告訴一名志願者,有一天她想寫的不是她過去的記憶,而是她的未來。
您個人從自己的經驗中學到了什麼?
不要預先判斷。我認為《Shukran,我的朋友們》是一部紙上公路電影,一本公路書。這是一趟實際的旅程,也是一次個人的旅程,充滿了學習,人們不斷以一種好的方式睜開你的眼睛,閉上你的嘴。有一次,一位難民對我說:「我的朋友,我來自伊拉克,而不是來自火星」。我認為這句話概括了整本書。
早在移民危機成為整個歐洲的新聞之前,西班牙就已經處於移民危機的最前線。您如何看待現在的情況?人們是否厭倦了這個問題,還是想要做更多事情?
恐怕什麼都有,但總的來說,我認為西班牙一直是個例子。我認識很多願意幫助有需要的人的人,他們不是為了幫助而來到西班牙,而是出於必要。對烏克蘭難民的反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儘管有人想知道為什麼對敘利亞或伊拉克人的反應不一樣。文化原因?宗教?害怕聖戰主義?關於這些觀點存在著許多錯誤訊息和偏見。我第一次了解到它是在 Katsikas。
歐洲各地移民和難民的待遇告訴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
歐洲記憶力很差。不久前,我們也從一個國家遷移到另一個國家,躲避炸彈,只是尋找一個工作的地方,並且能夠和平地生活。我認為我們認為福利國家是理所當然的,正如那位難民所說,我們邊界之外的一切對我們來說就像火星。如果說我在卡齊卡斯的日子裡學到了什麼的話,那就是明天戰爭就會波及你們,烏克蘭就是一個例子。缺乏同理心。讓我們記住,我們的世界並不是真實的世界。事實上,這是不真實的。
「Shukran 我的朋友」目前只能在西班牙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