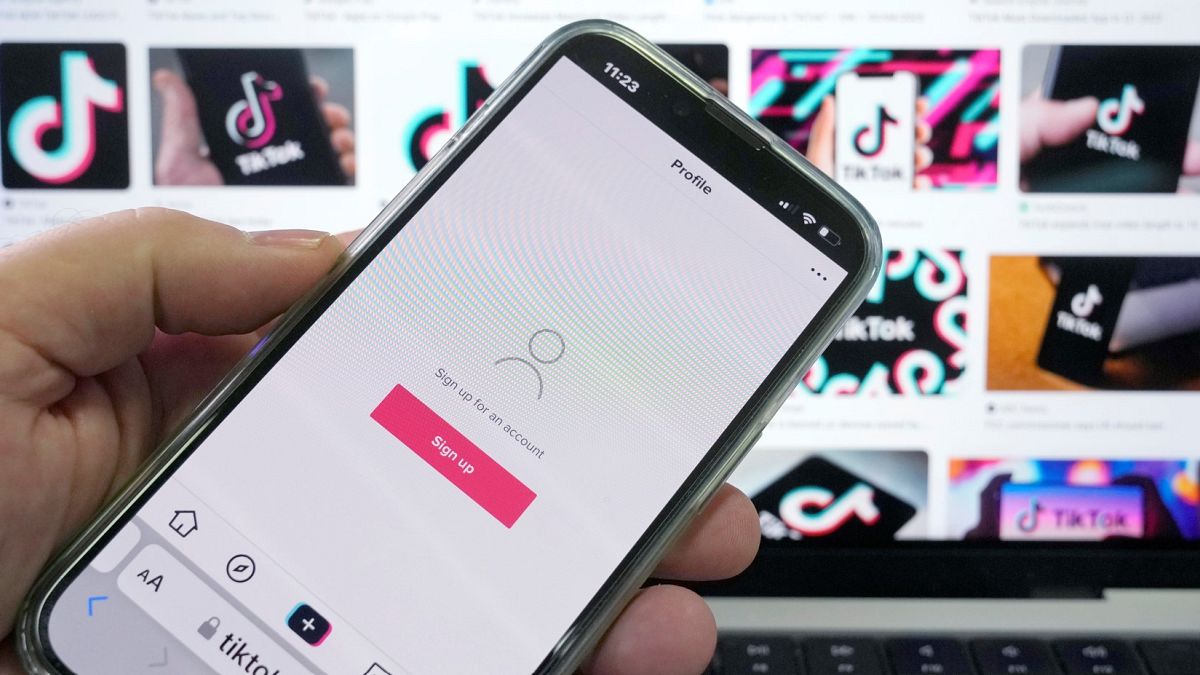2021 年 8 月,在美國撤軍和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後,受驚的阿富汗人不擇手段地爭先恐後地離開這個國家,包括緊緊抓住擠滿人的軍用貨機。
政府的倉促撤軍和隨後的垮台留下了權力真空,而塔利班完全填補了這一真空。民主進步。
一年後,在阿爾巴尼亞沿海小鎮聖金,一側是波光粼粼的亞得里亞海,另一側是高聳的山脈,數百名阿富汗難民陷入困境。
對他們來說,2021 年 8 月的恐怖仍然歷歷在目——痛苦地提醒他們,他們在確保阿富汗實現自由平等未來方面的作用化為泡影。
阿齊茲在講述美軍安排的撤軍和疏散時說:“這是非常混亂的。” “我和很多其他人都想,嘿,我們與美國政府有很多聯繫,這肯定只是一場等待遊戲,直到我們被帶出這個國家。”
他們不能——也不想——回到阿富汗,塔利班在那裡增強了他們的權力。
但許多人也不知道何時會收到美國簽證,這是一項專門對曾在美國工作過的人做出的承諾。
阿齊茲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全名,因為他在阿富汗仍有親戚,他們有一天可能想離開,或者可能面臨塔利班部隊的報復。他的母親和他一起住在聖金,兩人都對自己不確定的未來感到持續焦慮。
“如果我一年前就知道——我們被告知獲得簽證只能持續幾個月——它會持續這麼長時間,我可能會心臟病發作。”
空洞承諾的一年
阿齊茲清楚記得他和其他人在 2021 年 8 月之前感受到的災難即將來臨的感覺。
「我在喀布爾的一家顧問公司工作。我意識到[全國各地]的地區正在陷落,並且對於喀布爾陷落需要多長時間有不同的估計。但我們知道這將會發生,」他回憶道。
阿齊茲26歲,口才極佳,英語流利,對祖國政治有著深刻的了解。
他對那些隨意斷定阿富汗軍隊沒有參加戰鬥的人感到憤怒,理由是多年來「造成數十萬人傷亡」。他也對許多支持撤軍的分析師和專欄感到憤怒。
他在阿富汗美國大學學習資訊技術,並涉足心理學和經濟學等其他學科,同時也參與競爭性辯論比賽。
他一生多次搬家——從他的家人是難民的巴基斯坦回到家鄉坎大哈,最後來到喀布爾——他會說烏爾都語、達裡語、普什圖語,並在高中學習法語。
雖然他並不享有特權,但他表示,他的父親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透過文字遊戲教他英語,而他母親的教育工作塑造了他的世界觀。
阿齊茲和他的朋友們甚至在美國正式啟動撤軍之前就意識到該國局勢正在穩步惡化,並立即開始尋找離開的方法。
「我決定嘗試取得土耳其等地的簽證,但由於需求龐大,當時很難獲得簽證。隨著情況繼續惡化,我們決定去巴基斯坦,但這並不理想。我媽媽的簽證通過了,但我的簽證沒有通過,」他說。
“當我的家鄉坎大哈陷落時,那裡發生了激烈的戰鬥,我知道多米諾骨牌效應到達喀布爾只是時間問題。”
當美國總統拜登宣布撤軍計畫時,阿齊茲感到欣慰的是,他是一大群曾與政府或國務院合作的阿富汗人中的一員,西方國家也承諾保證他們的安全。
「由於我過去曾在美國和平研究所工作過,所以我有優先級1 和優先級2 分類,這是特殊移民簽證計劃的替代方案,該計劃要求人們在美國政府工作一年,以便獲得批准。 」有資格在美國重新定居,」他解釋道。
「除了在該研究所的工作之外,我還獲得了大學的獎學金,因此我利用這些推薦號碼來嘗試在離開喀布爾的飛機上獲得一席之地。”
喀布爾陷落的那天早上,阿齊茲像往常一樣去上班,發現從鄰省邁丹瓦爾達克逃出來的阿富汗坦克狀況不佳。 “交通狀況非常糟糕。謠言四起,說他們已經進城了,混亂蔓延開來。
「我聽說他們是從帕格曼進來的,那裡離我家很近,我媽媽也在第五區。我記得我急忙趕到那裡,我只能看到人們朝相反的方向朝機場走去。
“我甚至看到前部長和議員拎著行李跑向機場。”
他花了幾天時間回去,試圖進入停機坪並在飛機上找到一個座位。他回憶說,現場擠滿了人,人們幾乎無法呼吸。
「當美軍控制了機場時,他們沒有有效的方法來篩選允許誰進入。因此,那些勇敢地闖入機場的人——即使是以生命為代價——才是那些最終被疏散。”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塔利班不斷開槍,人們被擊中,每天都會有人死亡。所以第一批離開的飛機不一定是與美國有聯繫的人,他們只是設法通過的人。而那些有美國背景的人卻被排除在外,」他聲稱。
當他清楚地意識到與大學的聯繫不會成為他離開該國的門票時,他開始與各種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接觸。他乾巴巴地開玩笑說,填寫了這麼多表格,甚至聯繫了他從未聽說過的團體。
但隨著8月31日美國撤軍最後期限的臨近,他的恐慌情緒加劇。 “每一架離開的飛機都意味著我離被困更近了一步。”
雖然他和母親最初躲在親戚家中,但最終還是回到了家,因為擔心親戚或鄰居會告密他們,以討好塔利班。
喀布爾的一些人嫉妒那些與美國有聯繫的人所擁有的工作,或對國家的治理方式有深刻的分歧。去年8月之前,他從未聽過阿爾巴尼亞。
“我從未想過我最終選擇的路線會是我離開阿富汗的路線。”
主要關注婦女權利和教育的非政府組織 Vital Voices Global Partnership 聯繫了他,並告訴他,他們將為他和他的母親在 10 月離開該國的飛機上找到一個座位。他們告訴他他要去阿爾巴尼亞。
遊客和難民
阿爾巴尼亞是歐洲少數宣布打算接收數千名阿富汗難民的國家之一,另外還有科索沃和北馬其頓。
它是一個越來越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擁有 450 公里的海岸線、羅馬、希臘、拜占庭和奧斯曼時期的歷史景點以及鬱鬱蔥蔥的山脈。
將難民安置在該國容量最大的地方——夏季人滿為患的龐大度假村——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特別是因為費用由國家民主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或國際足總等組織承擔誰疏散了運動員。
聖金的拉斐洛度假村目前在酒店的一個專門區域收容了大約 800 名阿富汗難民,其中包括一個圖書館區、一個兒童區以及一個婦女和女孩區。
至關重要的是,該度假村擁有全天候保安,並設有銀行和超市等便利設施。
帕什塔納·拉蘇爾和阿齊茲一樣,參與了阿富汗民主努力的領導工作。在十月來到聖金之前,她是阿富汗兒童教育和護理組織(AFCECO)的執行董事。
「十個月前,也就是十月份,我來到了阿爾巴尼亞,」她告訴《歐洲新聞》。在她的飯店房間待了幾週後,「我厭倦了待在家裡無所事事,因為我的全家都回到了阿富汗。但在 11 月,我幸運地找到了這份針對女性和女孩的工作。
八月初,大泳池前的空間通常充滿了孩子和其他度假者大聲、快樂的哭聲。
在裡面,來自阿富汗各地的婦女們躺在五顏六色的豆袋上——遠離外面的炎熱——一邊聊天,一邊製作工藝品或編織,並與國際救援委員會及其當地合作夥伴 ARSIS 的協調員進行討論。
「我通常會朝九晚四在這裡擔任社區調解員,」這位 27 歲的年輕人解釋道。 「四點或五點後,我回家或和朋友一起去外面散步、去海灘或去購物。冬天,我們和社區裡的男孩女孩等朋友一起去遠足。我們非常喜歡它,我們參觀了阿爾巴尼亞的許多地方。
她喜歡待在聖金——儘管事實上,夏天有數以萬計的人湧入這座城市,晚上還會播放幾個小時的響亮音樂。她在這裡學會了游泳,並且喜歡每周至少游泳一次。
在來這裡之前,她也從未聽說過阿爾巴尼亞,除了被告知這裡有很多穆斯林,她會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這完全不同。阿爾巴尼亞人很友善,他們不在乎你穿什麼。我們是否戴頭巾,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她解釋道。
聖金是阿爾巴尼亞北部天主教徒佔多數的萊日縣的一部分,過去是重要的港口城市。萊日聯盟是一個由阿爾巴尼亞貴族組成的中世紀軍事聯盟,與奧斯曼帝國作戰,被認為是現代獨立國家的前身。
「我在這裡看到的最大區別是穆斯林和基督徒的行為相同,彼此之間沒有問題,」她評論道。
「宗教是阿富汗面臨的最大問題,少數群體普遍受到歧視,甚至不被允許上學。但這裡每個人都是一樣的,他們既慶祝穆斯林宗教節日,也慶祝基督教宗教節日。我喜歡它!
當她被問及家鄉的家人時,她的語氣發生了變化。
「我有兄弟姊妹。我有兄弟姊妹、父母,但不幸的是我的姊妹都在家。他們不被允許外出或上學。
「男孩們可以去上學,但即使他們也會抱怨,因為老師經常不在,或者因為沒有工資而不上課。即使他們出去了,每天都會發生爆炸。
她的兩個姐姐在塔利班接管之前就讀高中,第三個姐姐是記者,目前在巴基斯坦。
「當然,我夢想有一天他們會和我在一起。我的身體在如此美麗的國家,美麗的酒店,海灘,一切,但這並不讓我感到平靜或美好,因為即使當我走路時,我也在不斷地想著我的家人。關於我的兄弟姊妹。因為他們的未來已經被毀了。
被遺忘和不想要的
當被問及她認為自己的國家今後將走向何方時,帕什塔納很難做出積極的預測。
“我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為40年來我們一直處於戰爭狀態,政治局勢如此複雜,」她說。
阿富汗目前的大部分問題都可以追溯到1979年至1989年期間,蘇聯支持的參與該國共產黨政變的組織與西方支持的聖戰者組織之間爆發的代理人戰爭。
阿富汗人民遭受大規模戰爭罪行、強姦、種族清洗和酷刑,並受到代表兩個對立派系的人的虐待——一派聲稱支持嚴格的民主改革,另一派則希望維持對該國更多的宗教控制。
當時形成的裂痕,包括農村和城市人口之間的裂痕,至今仍然困擾著這個國家,並使該國陷入了從 1992 年到 1996 年的四年內戰。
塔利班於 1996 年上台,實際上控制了該國四分之三的領土,直到 2001 年被美國入侵推翻。
帕什塔納表示:“只要塔利班掌權,就不會發生任何變化,該國人民就沒有希望。”
「塔利班一直控制著阿富汗,即使我們有總統。但他們在村莊裡,控制著一切,但在城市裡,我們有很多機會,例如女孩學校等等,」她繼續說道。
與塔利班上一次掌權時不同,沒有人投入大量資金來幫助該國的民主力量從他們手中奪取權力。當被問及烏克蘭戰爭時——被廣泛認為是西方注意力轉移的原因之一——她強調了一個事實,即每個人都關心那裡正在進行的入侵。
「烏克蘭的情況非常悲慘,但他們很幸運,因為歐洲國家向他們敞開了大門。但對於阿富汗人來說,就連我們的鄰國也對我們關閉了大門,不允許阿富汗人前往那裡。
在內戰和各個不穩定時期,阿富汗人逃往遜尼派佔多數的鄰國巴基斯坦。
“上次他們說‘我們歡迎你’,但現在他們累了,他們不在乎。”
等待美國
雖然阿爾巴尼亞的一些阿富汗難民後來移民到加拿大,但剩下的難民中壓倒性的情緒是他們想去美國。
萊拉和她的兄弟雷扎都在聖金找到了工作,以便在等待簽證期間養家糊口。
他們被告知,有人有興趣將他們搬到密蘇裡州聖路易斯——這座城市已經擁有大量來自另一場戰爭(即波斯尼亞戰爭)的僑民。
波斯尼亞人被轉移到這座非常種族隔離的城市,試圖復興它,這也可能是他們對阿富汗難民感興趣的原因。
萊拉是一位身材高大、自信、迷人的女性,當歐洲新聞採訪她時,她穿著全粉紅色的連身裙,戴著頭巾。
「我是拉斐洛酒店的女服務員和餐廳的工作人員,」她說,並強調她的媽媽、四個姐妹和兩個兄弟在這裡感到安全。他們的父親在伊朗,他逃離家鄉馬扎里沙裡夫,後者在喀布爾之前陷落。
「我們希望,我們想去美國,」這位 20 歲的年輕人說道,「目前,一切都是未知數。我們不知道我們的處境,我們的未來,我們也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去美國。
「這對我來說是一種不好的感覺,因為每個人都很擔心,尤其是我媽媽。她老了,她一直在擔心,想著我們的未來。我們要去哪裡,我們的家在哪裡,我們要做什麼。
在阿富汗,她在巴爾赫大學農學院學習,戰爭爆發時她正在讀第一學期。她計劃盡快繼續學業。
閒暇時,她會和孩子們一起到兒童區玩耍。萊拉說孩子們很幸運,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擔心的少。 “他們在這裡是自由的。”
她的兄弟雷扎在聖金的另一家酒店工作。他學了一些阿爾巴尼亞語,並與拉斐洛度假村的當地工作人員愉快地交談。晚上不工作時,兩人都會出去。
但對萊拉來說,阿爾巴尼亞的一切都只是暫時的解決方案。雖然她的短期計劃包括搬到美國,但她希望有一天,她甚至能夠搬回阿富汗。
「我真的很想念我的國家。我真的很擔心不在場的朋友。我希望有一天和平會降臨到我的國家,我們會回來,不再搬到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