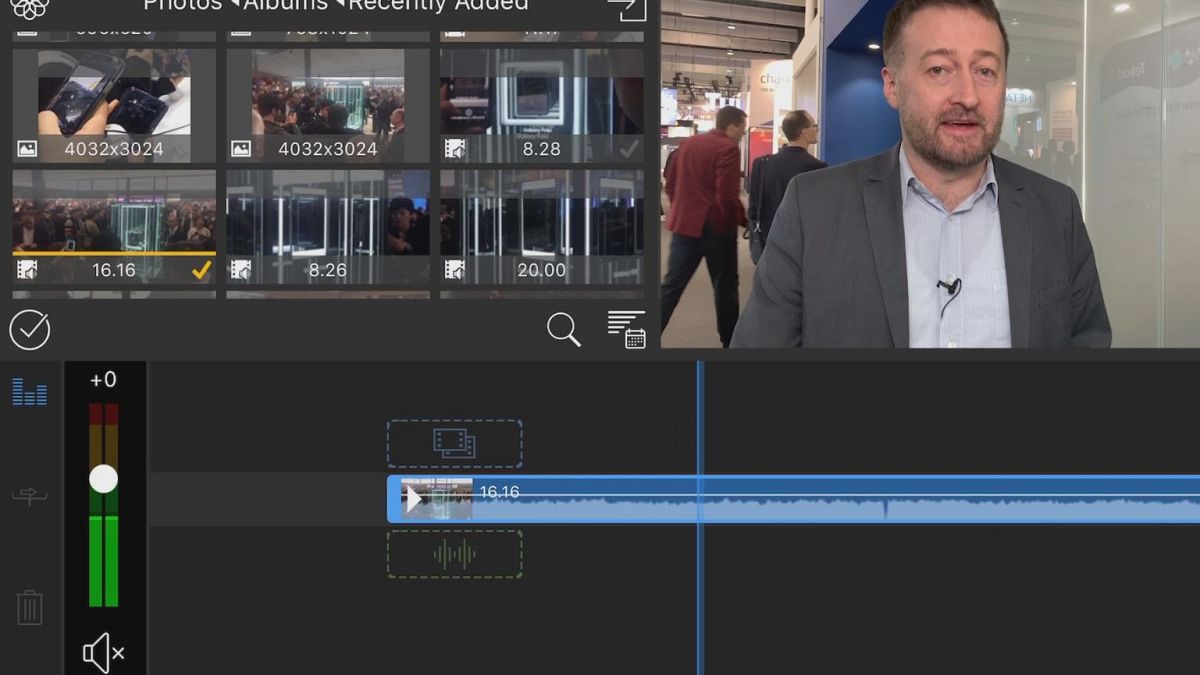這是一個陰沉的星期二下午 2 點,我正前往小丑的地下室觀看一系列彩繪雞蛋。
不,這不是恐怖電影的開頭——只是以國際小丑週(8 月 1 日至 7 日)名義進行的新聞報道,絕對不是我想看到倫敦一個古怪的地方的自私願望。
我要拜訪的小丑是 Mattie Faint,她是一位擁有超過 45 年經驗的專業表演者,也是最古老的小丑協會和小丑之友協會小丑國際 (Clowns International) 的受託人。
它收藏的服裝和道具曾經存放在達爾斯頓的聖三一教堂(也稱為小丑教堂),但在 2018 年的洪水後不得不搬遷。
我很慶幸我到達時他沒有穿著小丑服裝。這並不是說我害怕小丑——我喜歡他們色彩繽紛的服裝、化妝和花哨的愚蠢——但我也像許多人一樣,在童年時期觀看由斯蒂芬·金改編的90 年代迷你劇《IT》中提姆庫瑞(Tim Curry) 飾演的潘尼懷斯(Penywise) 所帶來的困擾。
當我向 Faint 簡短地提出這種恐懼時,他似乎有點受到侮辱:“小丑並不可怕!”
於是我們去了他的地下室;走廊上裝飾著復古的丑角畫作、自行車喇叭、非常小的小提琴和陶瓷小丑頭,引導我們進入一個小房間,小丑蛋登記器在那裡等待著。
收集了 250 多個畫有小丑面孔的雞蛋,小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正式記錄他們的外表和名字,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此類登記處。
「這些是戴這張臉的人的真實印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性格。
這一切都始於 1946 年倫敦人斯坦·布爾特 (Stan Bult),他創立了小丑國際組織,並開始在雞蛋上畫出其成員的面孔,作為存檔的一種方法。
「布爾特從來都不是小丑。他之所以成立這個組織,是因為戰後小丑經常在格里馬爾迪的墳墓周圍聚會,而他就在那裡拍照,」范特解釋道。
「他組了第一個沒有網路、幾乎沒有電話、每個人都寫信的俱樂部。所有的小丑都會在二月季節開始之前聚集在一起表達謝意,因為馬戲團是一項危險的工作。其中大部分都是根據生活而畫的。
布爾特一生畫了 350 個雞蛋,遺憾的是其中許多在多年來都被打破或丟失了。
「這些舊雞蛋其實是在皮卡迪利大街附近多佛街的一家餐廳裡。我1970年去過那裡,現在還記得它;所有這些雞蛋都放在中心的展示櫃裡。餐廳關門了,但隨後這位女士打電話給我們說:“我父親剛剛去世,我們在他的空餘臥室裡發現了這個陳列櫃,用螺絲固定在牆上,裡面裝滿了這些雞蛋。”您想購買它們作為收藏嗎?所以我們把它們買回來了。
此時,小丑國際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登記冊,其中包括原件的副本,畫在更堅固的陶瓷蛋上。
要完成這項任務,小丑必須向協會註冊,並支付 60 英鎊(71 歐元)購買兩個雞蛋,其中一個已存檔。他們的外貌和名字也由一個小委員會進行評估。
「一個女人想稱自己為可可,我們說,『不!你不能叫可可。在所有可供選擇的名字中,Coco 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小丑。於是她把名字改成了椰子。這是被允許的。
看著雞蛋讓人心曠神怡,一排排的笑臉在球根狀的時候更顯得迷人。每個故事背後的故事也是對小丑社群歷史的精彩洞察。
其中有已故美國著名小丑弗蘭克·薩魯托(Frank Saluto)的四眼和誇張的笑容,他的職業生涯持續了 46 年。
英國奧古斯特吉米·斯科特 (Jimmy Scott) 臉上綻放出燦爛的笑容,一頭橙色的捲發 吉米·斯科特是歐洲人對傳統紅鼻子、永遠笨手笨腳的喜劇馬戲小丑的稱呼。
我還了解到,Foottit 和 Chocolat 是 1900 年代巴黎馬戲團的表演者,其中 Chocolat 的真名是 Rafael Padilla,是法國最早成功的黑人藝人之一。
「這就是我的蛋,」法因特說,舉起一個紅鼻子、小亮片領結、戴著向日葵裝飾的大禮帽的蛋。
「事實上,我很快就設計出了自己的造型。我的大部分妝容都集中在 Coco 的臉上。
「我的眼睛和可可的很相似,我的嘴巴也很相似,但都是紅色的,周圍有線條。所以,是的,我從可可那裡汲取了靈感,我認為這是最好的術語。誰比較適合呢?
小丑表演
雖然我是來拿雞蛋的,但我留下來是為了小丑瑪蒂。
我們坐在一個雜亂的更衣室和一家專門從事小古董馬戲團的慈善商店之間的地方,聊了兩個多小時,談論他豐富多彩的生活。
搬到倫敦後,Faint 於 1971 年開始了他的小丑生涯:「小丑瑪蒂就是我。這是我的另一個自己。我不認為這是我的另一個自我。穿上你穿上的角色。你就變成小丑了。
他的第一套「雜色」服裝是由 Lindy Hemming 縫製的,她後來為各種服裝設計了服裝,從皇家賭場到黑闇騎士到旺卡,1999 年因其在顛倒黑白。
Faint 一直是一位天生的表演者,擁有戲劇背景,包括在沙夫茨伯里劇院出演《頭髮》,並擔任《洛基恐怖秀》的區域舞台經理,他還曾兩次前往非洲和日本演出。
19 年來,他一直在西奧多拉基金會擔任“咯咯醫生”,該組織僱用藝人幫助醫院裡生病的孩子。雖然工作的回報令人難以置信,但並非總是沒有問題。
「當我第一次在大奧蒙德街醫院開始工作時,我第一次穿上服裝就出來了。那裡站著兩個人,就像這樣【動作看起來悲傷]。他們看著我,我說:“你好!” [愚蠢的小丑聲音] 他們只是說,“好吧。”我說:“哦,你看起來不太高興!”他們說,『不,我們不是。我們的兒子剛剛去世了。
他們後來擁抱了,一切都很好,但一想到要處理如此緊張的情況——以及必須付出的情感代價——讓我想起了悲傷的小丑悖論,這是一些喜劇表演者使用幽默來管理和理解的理論。
對 Faint 來說,表演一直是暫時逃離人類棘手的存在主義的一種方式。
「一旦你穿上戲服,一切都消失了,因為你正在工作,」他解釋道。 “讓人們開懷大笑,這真是太棒了。”
就像看著一連串的泡沫綻放然後破裂一樣,凡特的軼事不僅閃爍著另一種生活的光芒,而且還閃爍著另一個世界的光芒。從兩次見到伊莉莎白二世(並用紅鼻子讓她咯咯地笑),到另一次關於一位小丑朋友幾十年後退休後卻在上班的火車途中心臟病發作的故事,它們無縫地在之間波動喜劇和悲劇。
雖然小丑的怪異面孔和誇張的動作可能會讓人感到害怕,但在一個更可怕的世界裡,他們的存在是完全有意義的。
它們體現了我們需要嘲笑這一切的嚴肅性;我們渴望成為自己之外的人,即使那個人有一朵小花。
裝傻有自由。
「我曾經路過一位在醫院工作的母親和她的兒子。我對他說:“你好!” [用愚蠢的小丑聲音] 他對媽媽說:“那個媽媽是誰?”她說,’那是偽裝成男人的小丑瑪蒂,’”Faint 說道,並補充道:“你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