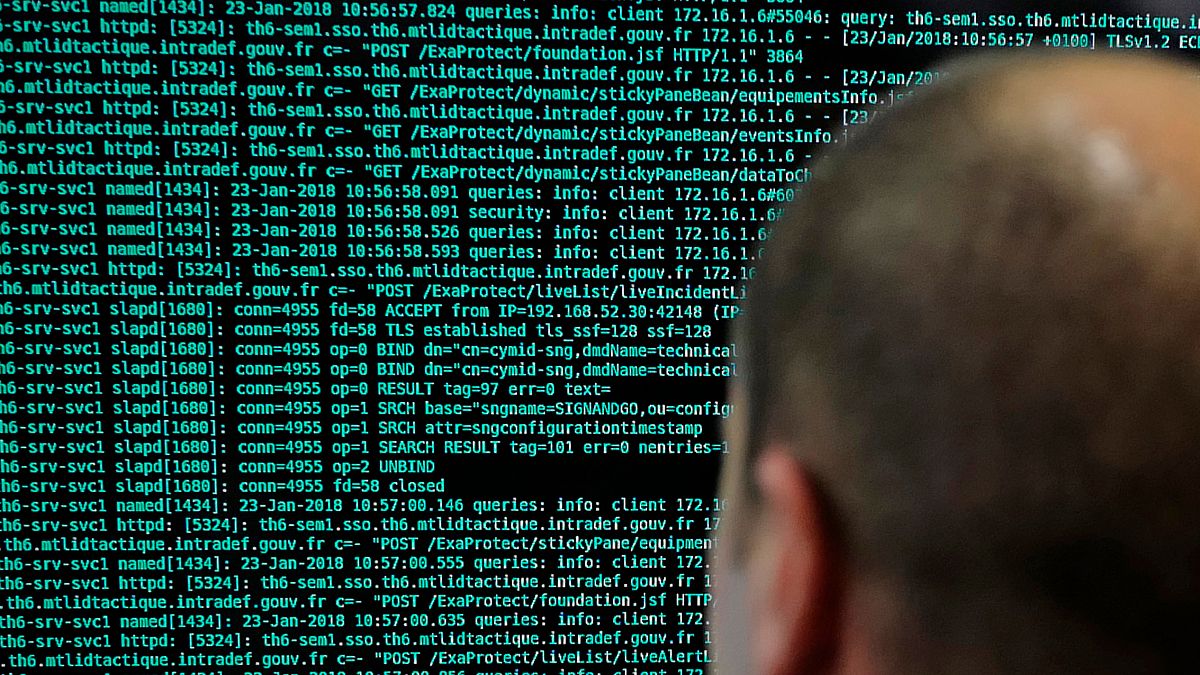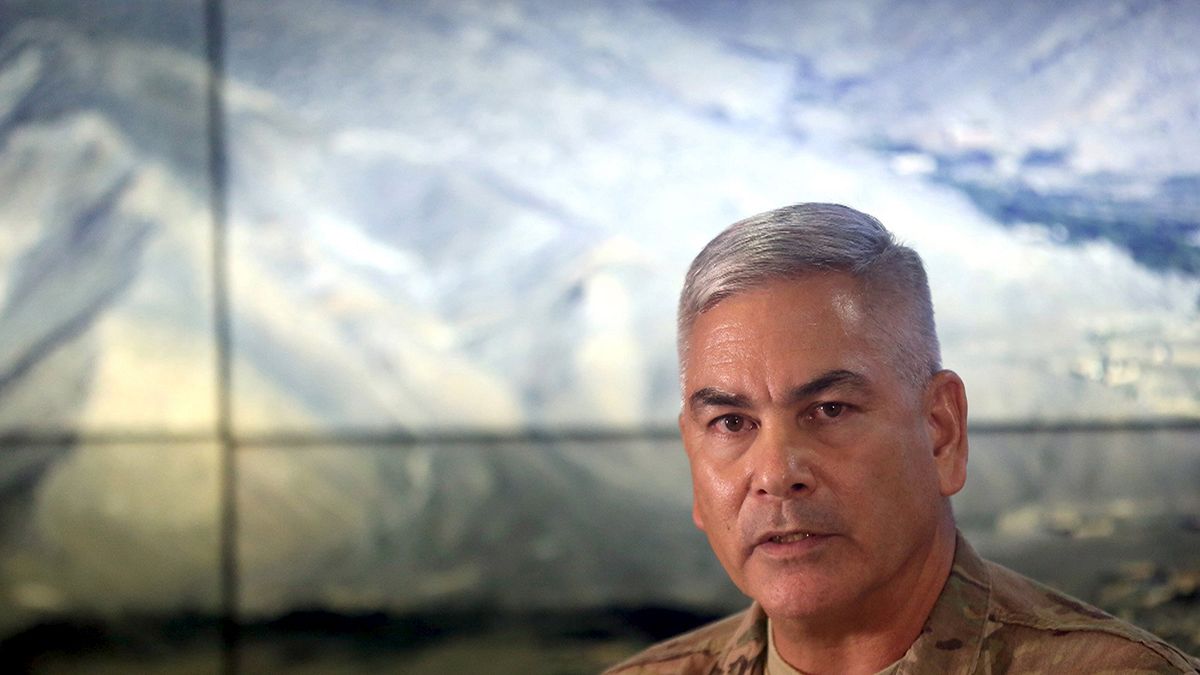4 月 4 日,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整個戲劇學校立即關閉。
現場與錄製藝術學院 (ALRA) 於上午 9 點毫不客氣地關門,並將其網站改為僅一份書面聲明,詳細說明了關閉的情況。
然而,相關的解釋卻很薄弱。許多教職員工和學生主要是透過推特得知學校關閉的消息。
這是一個關於戲劇學校消失後發生的事情以及所有受影響的人的故事。
學生面臨的殘酷現實
4 月 4 日是學生期中休息的第一個正式日子。確信當時大樓內沒有人,ALRA 關上了門並發表聲明。
ALRA 在聲明中聲稱,關閉是由於 2020/21 學年的虧損以及 2021/22 學年缺乏新的收入來源。
該大學還向所有學生發送電子郵件稱,ALRA 正在進入清算階段,並將停止教學。所有員工立即被解僱。
「我們知道 ALRA 的財務狀況並不好,」三年級學生 Akaash Dev Shamar 告訴歐洲新聞。 “我很確定他們停止僱用清潔工,因為有時大樓會變得很亂,當這個問題在學生會會議上提出時,我們幾乎看不到採取任何行動。”
只剩下一個學期了,像阿卡什這樣的三年級學生對剩下的學位以及戲劇學生準備的重要期末表演一無所知。
「我們每年要支付近 14,000 英鎊,所以我們會不斷詢問我們的錢都花到哪裡了。這是一大筆錢,老實說,這並沒有反映在我們得到的東西上。
預算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擠壓。去年,大規模重組導致許多老員工失業,並由新員工接任。
喬治·里士滿·斯科特 (George Richmond-Scott) 於 2020 年 9 月被聘為導演 MA 主管,但在此次改組中被晉升為現場和錄製表演主管。
「對於不得不離開的員工來說,這真是嚴峻且困難,」他回憶道。 「當時任何人所擔任的每一個角色都至少包含兩份(甚至更多)工作,這些工作都是核心工作,壓力很大。但沒有支撐結構。我們努力工作,盡最大努力向學生隱瞞這些現實。
缺乏溝通
ALRA 突然解體的核心最大謎團之一是學生和教職員工對這種情況一無所知。
在關閉前一個月左右,里士滿-斯科特和另外兩名老師直接聯繫了戲劇學校的高級領導團隊,擔心學校的財務狀況不穩定。
「我們直接詢問他們該組織是否遇到嚴重麻煩,我們是否可能關閉。我們根本無法讓他們說什麼。
不到一個月後,ALRA 的所有學生都沒有上大學。員工失業。自由工作者沒有任何清晰的報銷前景。
羅斯布魯福德 (Rose Bruford) 上台
消息公佈一小時後,另一所戲劇學校,羅斯·布魯福德,宣布他們將為每位在 ALRA 就讀的學生提供一個名額。 ALRA 學生必須在 4 月 20 日之前通知 Rose Bruford,他們想要一個繼續課程的地方。
學生辦公室 (OfS) 已聯繫 Rose Bruford,該辦公室曾與 ALRA 合作處理該校即將關閉的事宜。就在宣布這一消息的一周前,OfS 聯繫了 Rose Bruford。
「我們有幾天的時間來決定是否要介入並教授這些學生,」羅斯布魯福德副校長瑪麗奧利弗教授告訴歐洲新聞文化。
鑑於這些機構教學結構的相似性,羅斯布魯福德決定響應這項號召。
「我在學術界工作了幾十年,從來不知道情況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結束得如此糟糕,」她說。
Rose Bruford 的目標是為 ALRA 學生提供盡可能多的連續性。 ALRA 有兩個校區,一個位於倫敦,另一個位於英格蘭北部的維根。
羅斯布魯福德已經開始與維岡地方議會合作,保持北部校區對學生開放。然而,由於倫敦校區是從私人業主那裡租來的,目前尚不清楚他們是否能夠繼續在那裡教授 ALRA 學生。
羅斯·布魯福德也為因失去大學而感到困惑和創傷的學生提供了大力支持。
「他們只是感到震驚,需要大量的安慰和指導。對我們來說,這是為了給他們發言的機會,」Rose Bruford 學生招生和外部事務主管 Sally Elsmore 說。
其他組織也加緊幫助 ALRA 學生。
克拉珀姆的 Omnibus 劇院為 ALRA South 的學生提供了一個空間,從五月底開始表演他們的最後一年的演出。 4 月 27 日,ALRA South 第三年在歷久不衰的選角工廠 Spotlight 也舉辦了一場展示會。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會向 ALRA North 學生提供類似的機會。
前工作人員丹卡·埃切爾斯 (Daneka Etchells) 在推特上註意到了這個問題。 “我聽說前工作人員和前贊助人在聚光燈下為前 ALRA 畢業生舉辦了一個展示會。但它只提供給南方學生。而沒有向北方學生提供任何東西。他們被完全忽略了。”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對整個學校的支持如此響亮,而我們卻只支持那些能負擔得起倫敦培訓費用的人呢?”她繼續說。
“這的影響是危險的,坦白說是令人厭惡的。許多人僅僅因為費用而進入北校區。這些人存在什麼?”
學生費用消失
消息公佈後不久,推特上的討論就轉向了學生費用。每年近 14,000 英鎊的學費,學生們急切地想知道他們捐給 ALRA 的剩餘資金會怎樣花。
ALRA 敦促並提醒學生,如果他們不在 4 月 1 日截止日期之前交付下一學期的費用,可能會產生可怕的後果,這一事實加劇了這種情況。
學期學費截止日期三天後學校就關門了。
儘管關閉的消息是在要求繳納學期費用之後才宣布的,但 ALRA 的 SLT 肯定事先就知道關閉的消息。
至少在此之前一周,SLT 已與 OfS 直接討論了移交給 Rose Bruford 的必要事宜。
「我們承諾不要求任何學生重複付款,」奧利佛教授說。
但由於該公司正在進行清算,目前尚不清楚羅斯布魯福德是否會將任何費用轉移給他們。如果學生不選擇繼續在羅斯布魯福德學習,那麼收回學費的唯一希望可能就是透過漫長而曠日持久的法律訴訟。
自由工作者和員工陷入困境
「然後我問我是否應該在下一個夏季學期僱用自由工作者,」里士滿-斯科特繼續討論他上個月與 SLT 的會議。
自由工作者是戲劇學校工作的關鍵。戲劇學校的自由工作者網路通常由工作人員的個人聯絡人組成,他們受僱搭建舞台、編寫劇本和教授附加課程。
「我們被明確告知可以,」里士滿-斯科特說。 “所以我們做到了,並為下學期配備了充足的人員。”
隨著 ALRA 突然且毫無預警地關閉,尚未獲得報酬的自由職業現在將變成無薪。
Just Add Milk (JAM) 是一家支持工人階級演員的慈善機構,其創意總監 Liam McLaughlin 表示,他知道 ALRA 欠自由工作者數千美元。
「一位自由工作者被要求重寫表演劇本,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工作,但轉眼間就消失了,」他解釋道。
「現實情況是,我們的許多會員收回欠款的前景非常有限,」英國演員工會公平行業官員 Karrim Jalali 表示。
「這包括現有無償工作的資金,還包括因取消未來工作合約而損失的資金,以及那些因為認為自己與 ALRA 已有約定而拒絕其他工作的人的資金,」Jalali 解釋道。
由於 ALRA 已進入清算階段,它將進入債權人程序以收回學校債務。 “不幸的是,”賈拉利解釋道,“有效的方式是讓有保障的債權人優先考慮。”這意味著英國稅務海關總署、銀行、抵押貸款公司和貸款公司都得到了回報,但自由工作者可能會陷入困境。
「我最大的恐懼和擔憂是,人們被欠了數千英鎊,對他們來說,這就是他們有地方住、桌上有食物和養家糊口之間的區別,」賈拉利說。
員工處境並不好
優先債權人名單中通常會包括工作人員。但 ALRA 的教師和非教學人員就沒那麼幸運了。
「英國的就業法和商業法非常糟糕,無法為普通人提供保護,」大學和學院聯盟 (UCU) 區域支援官員阿曼達·薩克爾 (Amanda Sackur) 表示。
「如果你看一下優先債權人名單,你會發現這些都是大型機構,而不是個人,」她解釋道。自由工作者位於清單的底部。但由於 ALRA 也立即解雇了員工,因此他們的優先事項並沒有高出多少。
「ALRA 的行為令人震驚,」薩克爾說。 「解僱他們。如果他們沒有被解僱,他們就會成為優先債權人。但這對 ALRA 來說是最簡單的事。他們切斷所有聯繫並逃跑。
員工將能夠申請一段通知期,儘管他們可能無法從 ALRA 獲得通知,但經過漫長的過程後,政府可能會向他們提供補償。
還有一個問題是 ALRA 員工是否能夠繼續在 Rose Bruford 的工作。在我與副校長瑪麗·奧利弗的談話中,除了該機構正在評估這種可能性之外,她無法證實任何其他事情。
一個陷入困境的組織
對於一個多年來飽受管理不善困擾的機構來說,這是不可避免的嗎?
在ALRA最最近公開發布的審計截至2020 年8 月31 日的完整帳目,截至2025 年8 月的五年計畫讓受託人相信ALRA 「在可預見的未來(不限於簽署這些財務報表之日起12 個月)仍將持續經營。 」
一位匿名評論員表示,至少十年來,ALRA 一直是個糟糕的雇主。對該機構來說,過去兩年並不輕鬆。
2020年3月,一封公開信發表了詳細指控有關學校系統性種族主義的指控。在受到批評後,董事會委託進行了外部審計,以報告有關指控的調查結果。
學校校長阿德里安·霍爾 (Adrian Hall) 於 2021 年 1 月辭職。
2021 年 5 月,內部種族主義報告得出結論,學校為有色人種學生創造了一個「羞辱性、敵對性和排他性」的環境。還有指控稱北校區的 ALRA 老師對學生進行性騷擾。
2021 年 5 月 31 日,ALRA發表聲明回應聲明稱,學校「得知這些指控感到心碎」。
「這些指控是針對不再在 ALRA 工作的工作人員。學校的高級領導層已對不當性行為的指控展開內部調查,並正在公開徵集信息。”
專業表演碩士學生薩菲·安德魯斯講述了她在“敵對”環境中的經歷。
「我抱怨得越多,關於我的殘疾的微侵犯或評論就越多,」她描述道。
「四月從封鎖返回期間,我經歷了很多事情,我失去了一位家人,我以為他們根本不在地球上。這太可怕了,ALRA 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支持我。我從來沒有得到過特別針對我的運用困難的支持,直到 10 月中旬才得到支持,因為我知道課程將於 12 月初結束。
然後是人員變動。其他不願透露姓名的歐洲新聞文化評論員質疑,除了管理不善之外,是否還存在腐敗。
里士滿-斯科特回憶起與 SLT 的溝通問題。 「他們與其他教職員工或學生溝通不佳。他們無法聯繫到,這不是健康的操作方式。
2021 年 10 月,ALRA 開始尋找新東家。但在與相關方協商後,校方表示此目標不可能達成。
實際出售該機構所投入的工作量令人懷疑。 「他們顯然優先考慮尋找買家,因為沒有人聽到任何關於他們尋找買家的傳聞。這很不尋常。通常謠言四起。我懷疑他們並沒有仔細觀察,因為他們不想讓消息傳出去。
臨時 SLT 的任命包括擔任董事會主席的 Harry Cowd、擔任臨時校長的 Ellie Johnson-Searle、擔任臨時註冊員的 Sara Doherty 以及擔任臨時首席營運官的 Elizabeth Sell。歐洲新聞台曾嘗試與所有這些人聯繫,但截至發稿時尚未成功。
政府和治理的失敗
本文訪談的許多人都對設立學術機構以吸收費用、董事會突然消失的道德提出質疑。
「那些擔任過董事的人將帶著他們完好無損地創辦另一家企業的能力離開,」蘇克說。
「教育私有化存在嚴重問題。如果依賴收費模式,機構可能會破產,而政府正在讓它們破產。
「這不是第一家失敗的私立教育公司,也不會是最後一家。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教育模式。你購買的東西並不取決於消費者的態度,而是要改變人們及其生活,」她說。
由於高等教育機構需要依賴收費而不是政府支持,它們開始像企業一樣運作。 「這表明政府不會介入並救助高等教育機構,」奧利佛指出。
西北大學官員保羅·利弗西 (Paul Liversey) 在與 Equity 討論這個問題時認為,需要為學生貸款提供更多擔保。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該組織破產,資金就會以某種方式得到保護。它與大型組織的金融貸款不同,如果該組織破產,大型債權人可以提供保護。
「我們希望為自由工作者和學生貸款提供更大的保障。推動為公共教育提供更多資金,同時透過裁員提供盡可能多的支持,以收回他們的資金和心理健康支持,」利弗西說。
英國藝術的未來
「本屆政府對藝術產業的敵意也存在問題,」薩克爾說。
她注意到在大流行期間向一些劇院和博物館提供的小額資金。這筆錢足以讓關閉的劇院保持財政償付能力,但通常為這些機構工作的人卻沒有錢。
同樣,她質疑為什麼戲劇學校一直英國政府資金不足。鑑於教師對課程的參與度很高,戲劇學校需要更高的教職員工與學生的比例,但資助模式尚未認識到這一點。
「藝術部門為國家帶來了重大的經濟、教育和文化利益。但政府不會承認或支持這一點,」她說。
失去 ALRA 的影響也可能對下一代戲劇從業者產生影響。
對於 ALRA 的第三年,他們的第一年將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前幾個月開始,因此未來兩年的課堂時間僅限於線上課程。現在,終於回到學校第三年了,學生的學習完全被這件事打亂了。
ALRA 位於維根的校園也是一所罕見的戲劇學校,可供英國北部的工人階級演員入學。在如此悲傷的情況下失去它可能會影響未來學生對戲劇事業的希望。 「這個行業的代表性已經嚴重不足,發生這樣的事情並不會鼓勵任何人進入這個行業。它不會改善這個行業的多樣性,」利弗西說。
“沒有豐富背景的人會對嘗試這個行業的職業持謹慎態度,因為當這樣的事情發生時,他們就會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