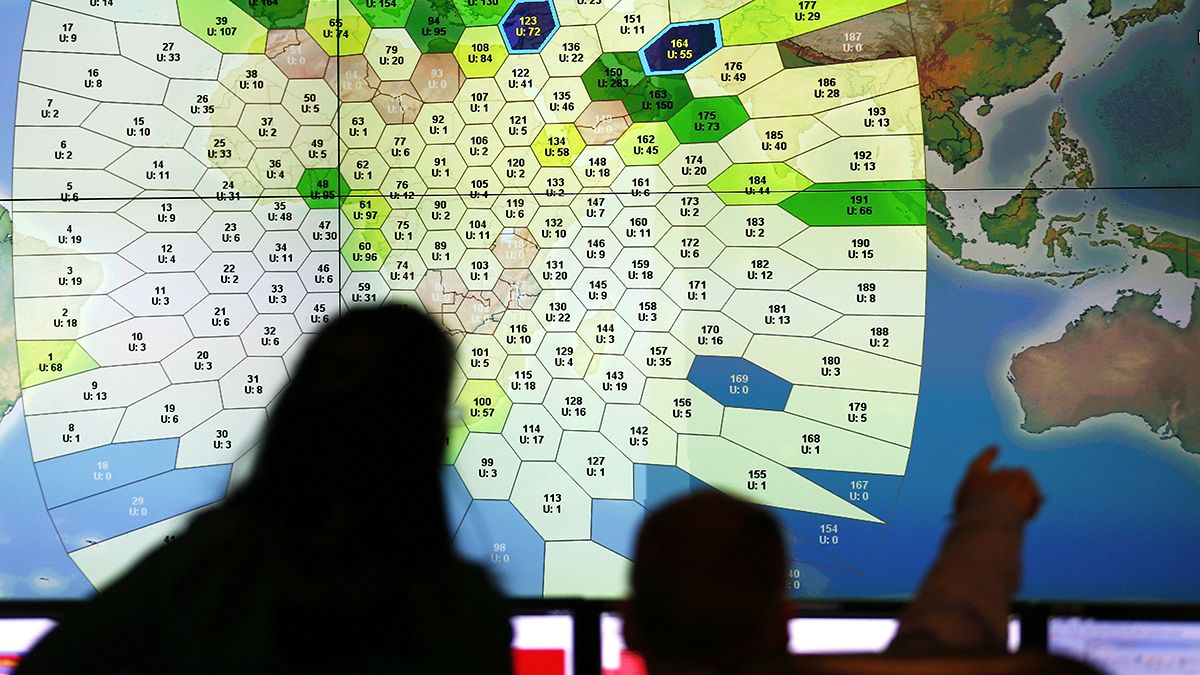當傑爾吉·哈布斯堡(György Habsburg) 2021 年作為匈牙利新任駐法國大使首次接受法國媒體採訪時,一些讀者通過提起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Antoinette) 的記憶,展示了法國和匈牙利之間的仇恨由來已久。
路易十六的令人憎恨的妻子於1793 年法國大革命後的恐怖時期被處決,她是奧匈帝國統治者瑪麗亞·特蕾莎皇后和弗朗索瓦一世皇帝的女兒,也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傑爾吉的遠親。
然而,儘管事實上可能是那些《費加羅報》讀者的遠親讓瑪麗安托瓦內特擺脫了困境,但傑爾吉·哈布斯堡王朝並不認同他們的敵意。
「感謝上帝,我們有一個自由的歐洲,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告訴歐洲新聞。
不管怎樣,他說,他第一次在法國媒體露面後收到的負面評論比他在奧地利接受媒體採訪時收到的負面評論要少得多。 400 多年,直到1918 年11 月帝國解體。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匈牙利與法國的關係有所改善,更不用說自法國大革命以來,但哈布斯堡王朝告訴歐洲新聞,他意識到法國媒體和公眾仍然對匈牙利抱持敵意。
他說,作為駐法國大使,他的任務之一是提高新家對法國的看法,並強調,除了報紙之外,2021 年兩國之間的聯繫也很牢固。歐洲新聞台的諾拉‧謝努達 (Nóra Shenouda) 與他坐下來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
您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王朝的後裔,是皇帝和國王的孫子,是奧匈帝國最後一位王位繼承人奧託的兒子,奧託在創建歐盟的最初階段就在那裡。
然而今天,匈牙利政府因其歐洲懷疑主義而受到批評。你覺得很矛盾嗎?
“我不認為匈牙利政府非常持歐洲懷疑論。我看到一個政府批評歐盟的進程和政治結構——我認為這是合法的,因為歐盟有許多問題,很多事情效果不佳,但哪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我在匈牙利沒有見過任何政治人物能夠想像不加入歐盟會更好。我沒有看到任何離開歐盟的意圖。我們身處這個大家庭,重要的是要解決可以做得更好的問題。
「匈牙利並不單獨代表自己的立場,而是透過維謝格拉德國家的合作,共同代表中歐大國的立場。他們之間存在爭論,但如果他們代表維謝格拉德的共同立場,機會就會大得多。
您在接受《費加羅報》採訪時表示:我們認為歐盟最近出現的一些做法或決定與歐洲開國元勳的基本理念不符。
「不幸的是,歐盟希望對太多細節產生影響。我們忘記了歐盟最重要的因素是和平與安全。讓經濟在國家之間運作良好固然有幫助,但和平與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在上個世紀,經歷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非洲大陸向東西方分裂,而歐盟在這一切之後所取得的成就令人驚嘆。但不幸的是,我們常常忘記,最重要的是歐盟的重要原則是和平與安全,我們還要處理太多其他問題。
您自三月以來一直擔任匈牙利駐巴黎大使。您在任期內希望實現什麼目標?
「從7月起,匈牙利將接任V4國家輪值主席國,這樣就有可能讓V4獲得更大的知名度。當然,明年法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將非常重要,並將提供許多機會讓匈牙利獲得更多關注。
「那麼法國總統選舉將與匈牙利議會選舉同時舉行。參議院選舉將在2023年舉行,這可能是稍微平靜的一年,但2024年是匈牙利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一年,同時奧運會將在巴黎舉行,因此未來幾年代表匈牙利的機會會很多。
「不幸的是,在法國,媒體對匈牙利形成了不太有利的形象。我們必須努力改變這種狀況。
在接受《費加羅報》採訪時,您回顧了歷史上匈牙利和法國關係的一些有趣細節,包括法國路易十四在拉科齊獨立戰爭期間向匈牙利提供軍事援助,以幫助您對抗您的祖先。
您也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兩國在歷史上處於對立的立場。匈牙利人的心目中對法國人有一定的負面形象,而法國人對匈牙利人的形像也有偏見。身為大使,您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我看到媒體上有一些批評,但當我們審視全方位的關係時,我們發現貿易和經濟關係非常好,匈牙利有很多法國投資者:匈牙利提供了超過4萬個就業機會。其中550 家法國公司在匈牙利開展業務。氣候議題對兩國來說也都非常重要。
「至於我的個人背景:我的父親在洛林首府南錫結婚,並與這個法國地區建立了非常特殊的聯繫。當他在歐洲議會工作時,他是法語工作組的成員。
“我在法國遇到的許多政治家都曾與我父親在歐洲議會共事,因此我與他們建立了私人關係,這對我的工作很有幫助。”
距離你父親 7 月 4 日去世已經十年了。他是全世界備受尊敬的人物。遺產對您目前的工作有何幫助?
“這很有幫助。我非常想念我的父親,他是最好的輔導員。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挑戰、困難、問題……當我仍然能夠詢問父親對特定政治局勢的看法時,該有多好。
「他活到了98歲,出生於1912年——當時奧匈帝國還存在。1916年他成為王位繼承人,所以他確實了解上個世紀的整個歷史。而且他總是他在政治上很活躍,當當英國脫歐、新冠肺炎(COVID-19) 和其他歐洲問題出現時,如果能了解他的觀點,那就太好了。
「我非常懷念的是他對上個世紀發生的事情的了解。我試著像他一樣思考。他總是樂觀的,我不記得他曾經對某些政治進程持悲觀態度。我也努力成為樂觀,我總是嘗試處理效果良好的問題,也就是問題更容易處理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