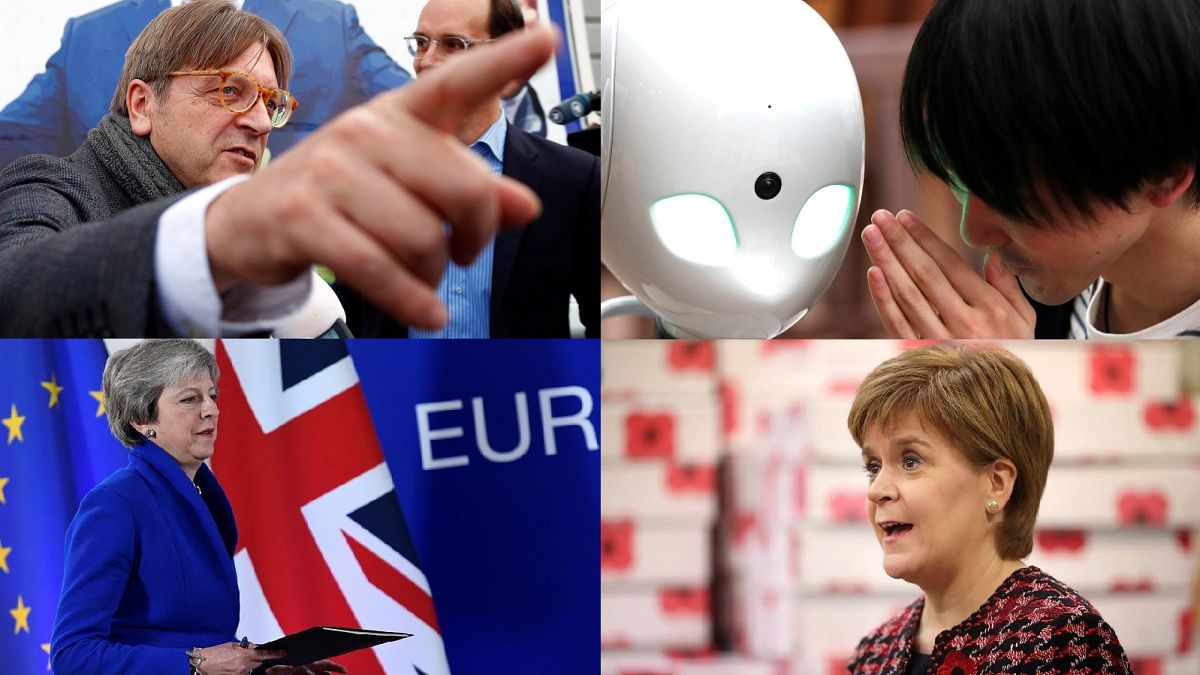我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卡的公車站的陰影下等待,看著陳列的鞋帶和運動鞋。不久後,我看到一個男人滿臉笑容地向我走來。他的脖子上掛著一條木製念珠項鍊。這是馬馬杜,一位 30 多歲的塞內加爾年輕人。
一位共同聯絡人告訴我,他大約三個月前被驅逐出歐洲。現在,Mamadou 輕鬆地帶路,開玩笑地問我來自沃洛夫州的哪個地方,以測試我的語言技能。上個月他一直住在達喀爾的這個房間。
我對他最近返回塞內加爾後的處境相對輕鬆感到驚訝,因為我讀到並聽到了一些關於被驅逐者艱難處境的故事。當我仔細詢問他的情況時,他總結道,回來並不容易。但他說:「真主啊。我從不低頭,不,不,不。我還年輕。我是一個男人。未來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強硬的男性理想,例如需要堅強、不流露情緒以及必須承擔養家糊口的負擔,有時被認為對男性和女性都有害。
但是,如果像馬馬杜這樣比他計劃的更早中止移民旅程的所謂邊緣化男性,以及他們的周圍環境也以同樣的男性理想來應對他們共同的苦難和痛苦,該怎麼辦?
身為一個男人挑戰被驅逐出境的恥辱
在塞內加爾,移民既是一種恥辱,也是一種特權。它可以提高社會地位,但也會導致恥辱和痛苦,例如在移民計畫流產之後。
在塞內加爾,作為被驅逐者返回的返回者常常被描繪成罪犯,或者愚蠢到被遣返,或者由於在國外的經歷而面臨患精神病的風險。他們也面臨在祖國重新出發的困難。
馬馬杜和我遇到的其他回返者在談論他們的移民經歷時經常提到男性理想。儘管他們現在或以前的處境很困難,但他們很少挑戰堅強、養家糊口和忠實穆斯林的想法。
馬馬杜與塞內加爾記者的對話就是一個例子。記者在電視採訪中詢問馬馬杜回到塞內加爾後過得怎麼樣。馬馬杜回應:
「我被驅逐到塞內加爾這一事實並沒有傷害我個人。但當我想到我的家人指望我、希望我成功時,我就很難過。我沒有結婚,但我有父親、母親和姊妹們依靠我。但我承認,這並不容易。
他並沒有因為驅逐出境可能帶來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而失去男性氣質,而是將自己描繪成一個想要為他人做好事的人。
透過這樣做,他可以因其團結和男子氣概而受到讚揚,並挑戰被驅逐者是受害者、罪犯或愚蠢的觀念。
他現在可能無法實現所有男性理想,但他過去做到了,並且計劃在未來再次做得更好。這可能意味著他可能會像第一次被驅逐後一樣再次離開塞內加爾,但目前他似乎正在尋找留下來的方法。
馬馬杜對他第二次被歐洲驅逐的經歷相對開放,儘管他並不總是談論這件事。他說:“當人們不問時,我不會告訴。”
壓抑情緒的力量和痛苦
作為男性理想的一部分,沉默可能既痛苦又充滿力量。
當我遇到 Oumar 時,我更好地理解了這一點。他告訴我他在歐洲學習,然後回到塞內加爾工作。
我們見面後不久,他突然再次離開塞內加爾繼續學業。幾年後我見到了他,直到那時,奧馬爾旅程中不言而喻的部分才被揭露:他在歐洲的第一次逗留並不完全合法。他第一次去那裡時,曾以「無證件」的身份生活過一段時間。他後來被驅逐出境。
事實證明,我並不是奧馬爾唯一沒有向其講述完整故事的人。他很少透露這個秘密,因為他擔心人們不理解或認為他在抱怨。
身為塞內加爾的兒子和穆斯林,他認為不發聲是一種文化和宗教義務。雖然他突然回來不是什麼可以直接問的話題,但人們還是有想法的。
「每個人都知道,但沒有人知道。在我們說出來之前,我們不知道,」他說。他發現自己的負面形像以及人們不與他說話的事實很殘酷。
必須將自己的感受保密是很困難的,他也認為沉默是證明自己價值和展示他如何在歐洲成長的一種方式。為了展現自己處理困難情況的能力,他秘密地規劃了一次新的歐洲之旅。他只在離開當天告訴人們他要離開。
這次新的旅行使他再次成為一位著名的年輕人,並讓他擺脫了與第一次不合時宜的回歸有關的負面聯想。
「它拋開了恥辱和一切,所以他們忘記了情況並想到了當前的情況,」他說。
在塞內加爾,強勢和養家糊口的男性理想給馬馬杜和奧馬爾帶來了痛苦和磨難,但這些理想也為他們提供了重新樹立男子氣概的機會。雖然這對所有回來的塞內加爾男性來說可能並不可行,但對某些人來說是可行的。
卡利安·斯特里博斯是一名博士學位。荷蘭馬斯特里赫特大學的候選人。在她的論文中,她研究了塞內加爾的男性回返者如何敘述和表演與男性氣質相關的移民經驗。她與達卡謝赫·安塔·迪奧普大學合作,在塞內加爾花了近一年的時間與回返移民過程中的各個利益相關者(尤其是回返者本身)進行交談和接觸。 _
____________
查看文章中表達的觀點僅代表作者的觀點。
您是在非洲工作的領域公認的專家嗎?您是非洲人後裔嗎?您想分享一個挑戰傳統男性觀念的個人故事嗎?給我們發電子郵件:[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