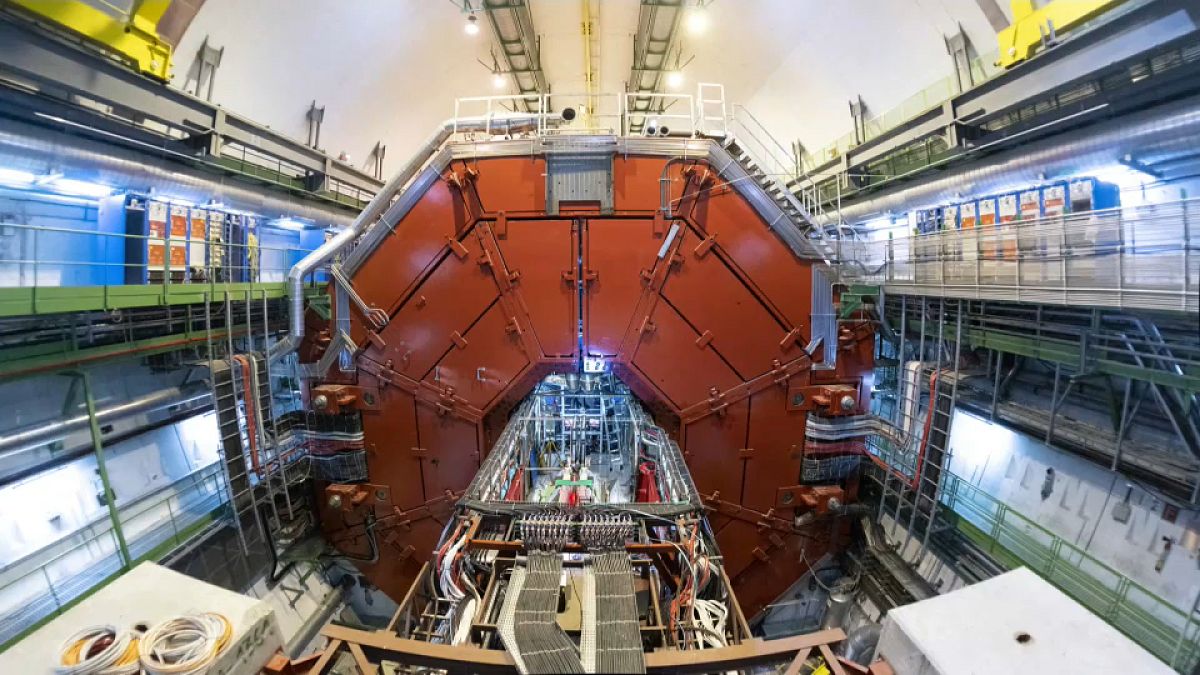兩年前的 7 月 22 日,奧托·洛維克聽到附近一座小島上傳來槍聲。他跑向遊船碼頭。
「當我們到達時,已經有兩個女孩從島嶼上游到這裡來了。他們說於托亞發生了槍擊事件。他們說有人被殺了,所以我們跳上了船。我們開始救起溺水者或被擊中的人,將他們放入船上。
奧托和其他幾人成功救出了 250 多名在於托亞島參加青年工黨夏令營的挪威年輕人。
當一名孤獨的槍手進行瘋狂射擊和殺戮時,於托亞變成了一場血腥屠殺。
於托亞島將造成 69 人死亡,奧斯陸的炸彈爆炸將造成另外 8 人死亡。
「我記得當我們第一次去島上然後回來時,在我的船上我想,那些該死的塔利班分子,那些該死的伊斯蘭主義者。我確信那是恐怖——伊斯蘭教。
但他和許多其他挪威人一樣,被證明是錯的。
當發現唯一的殺手是一位名叫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的右翼極端分子時,這個只有五百萬人口的北歐國家陷入了震驚。
布雷維克為殺害年輕受害者辯護,因為他們屬於執政的挪威工黨的青年部門。
正如當天早些時候奧斯陸發生的造成 8 人死亡的炸彈爆炸一樣,貝林的目標是政府。他指責政府在應對他所認為的挪威和歐洲其他國家日益增長的伊斯蘭教威脅方面過於軟弱。
儘管許多人認為布雷維克的行為屬於瘋子,但布雷維克被宣布神智清醒,可以接受審判,並被判處最高 21 年監禁。
如今,挪威人仍在思考「為什麼選擇挪威?」這個問題。全國性的反省在網路上找到了一些答案。
拉爾斯·古勒(Lars Gule) 是一位網路極端主義專家:「關注他的法庭案件非常有趣,因為當他被要求介紹自己的背景、受過什麼樣的教育等等時,他聲稱讀過很多書——『哦是的,我學過』。當他被要求識別書籍和作者時,所有資訊都來自網路。當我們查看他所謂的宣言或綱要時,我們可以看到他曾經造訪過什麼樣的網站。它們是右翼、右翼激進或右翼極端主義網站。那是他獲取情報的地方。那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世界觀的地方,」古勒說。
布雷維克大屠殺後,羅尼·阿爾特離開了「挪威國防聯盟」。他說,他對這些殺戮感到震驚和厭惡,並對媒體和警方最初試圖將他與布雷維克聯繫起來感到憤怒。如今,他建立了一個名為「挪威自由黨」的新網站,該網站對挪威的伊斯蘭威脅發出警告。
羅尼說,雖然挪威20萬穆斯林中大多數是溫和派,但大約有30名極端分子是危險的。
羅尼認為他的組織不是右翼極端主義者。他有支持。他的網站每天點擊量超過 5,000 次。
「大多數挪威人民都同意我們的說法。是媒體將我們塑造成極端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的形象。但我們只是熱愛我們國家的普通挪威人。大多數挪威人意識到政府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他們只是給予、給予、給予那些利用這個系統的人。政府不求任何回報,不求任何回報,」他聲稱。
哈瓦爾·阿卜杜勒·拉赫曼·佩特森(Halvar Abdel-Rahman Pettersen) 對政府感到憤怒,但出於不同的原因,他最近皈依了伊斯蘭教,但他表示,多年來他在精神上一直是穆斯林。哈爾瓦爾指責奧斯陸對右翼極端分子過於寬容,並壓迫世界各地的穆斯林。
他說,在7月22日的殺戮之前,他已經準備好加入恐怖主義戰爭。他想購買一座農場,這是獲得布雷維克用來製造奧斯陸炸彈的肥料的唯一方法。
現在他說他的鬥爭是透過言語和網路進行的。
「在此之前的十年,我沒有與像你這樣的人(媒體)交談過。我沒在電話裡說話,只是胡言亂語。我沒有在網路上做任何事情,只是廢話。我成為了一個公民團體的主要成員,一個非常保守的團體,我做了所有正確的事情。我躺得很平。因為,是的,我計劃好了。我已經走了那麼遠,我一直在尋找這個農場,但當然,7 月 22 日之後你就沒有機會了。
挪威長期以來一直以開放和民主的社會而自豪。這是一個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在國內外分享其財富,許多人聲稱這個國家最不會發生極端主義或恐怖攻擊。
今年,與往年一樣,工黨青年黨成員正在為夏令營做準備。除此之外,2011 年後,每一年都與往年不同。短期內不會再回到於托亞了。
大屠殺期間,AUF 工黨青年黨主席 Eskil Pedersen 就在島上。他表示,目前還沒有從這場悲劇中學到教訓。
「在挪威發生的事情可能會在每個國家發生。因此,我們需要就開放社會中存在極端分子這一事實進行公開討論。所有支持多元文化社會的人都應該站起來,不要容忍網路上的辯論被種族主義觀點的人所佔據。
弗雷迪·李和凱瑟琳·李在於托亞殺人事件中失去了一個女兒和一個妹妹伊麗莎白。凱瑟琳也在島上。她受傷了,目前仍在恢復中。
年輕的倖存者感到內疚和疑問,尤其是當涉及槍手殺人方式和原因背後的邏輯時。
「我決定爬到水邊,這樣他就看不到我了。但我沒能及時到達水邊。就在那時,他從我的背部開了一槍,子彈從我的腹部射出,穿透了我的一個肺部。在那裡我完全暴露在外,暴露在外。他看到了我,但沒有再向我開槍。我暈倒了,」她非常緩慢地說。
事實上,布雷維克確實回來了,又朝她的手臂開了一槍。她姐姐的葬禮被推遲到她出院為止。
今天,弗雷迪說,他現在才能夠為伊麗莎白感到悲傷——作為一個父親,對如此公開、悲慘和有爭議的死亡感到悲傷。
「我不生氣,因為這需要太多精力。但我對當局及其缺乏支持感到非常失望。他們一直做出這些承諾,但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現在我們即將舉行選舉,我們卻被遺忘了。我們只是更廣泛的政治遊戲中的棋子。
九月,挪威將舉行於托亞屠殺事件以來的首次選舉。
有些人表示,政府本可以採取更多措施來預防殺戮事件,因為警訊已經存在。
但對許多其他人來說,這是一場悲劇,挪威仍在尋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