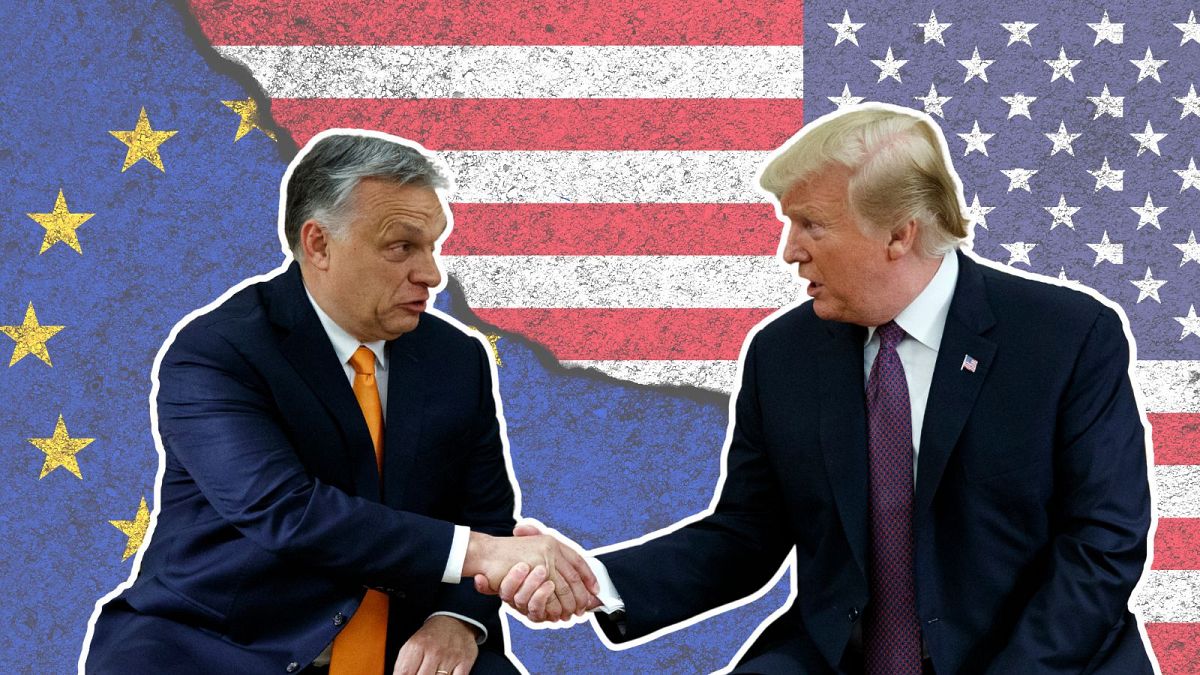我第一次接觸有毒的男子氣概可以追溯到我還是個小孩的時候。
我和父母在商場裡,想騎遊樂園裡那種會移動的機器。這是一隻小唐老鴨。我父親認為這個「玩具」不夠陽剛,所以決定讓我再搭一次,那就是一架離地面稍高一點的直升機。它更大,而且實際上對小孩子來說不安全。當直升機開始移動時,我非常害怕,無法停止哭泣和大喊,我伸出雙臂讓他帶我回去。但他沒有,反而笑了。這種情況讓我產生了一種新的恐懼:懼高症。今天我仍然感到眩暈。回想起來,也許這是他扭曲的想法,讓我進入一個艱難的世界。
在非洲長大的酷兒孩子是危險的,因為關於男人在社會中的行為的所有規則。對我來說,他們特別嚴格。
我的父親是一名軍人,他所參考的大多數男性家庭成員也是如此。他的名字加斯帕 (Gaspar) 繼承自他的叔叔加斯帕·達席爾瓦 (Gaspar da Silva),他是一名陸軍將軍。
這種軍事般的能量是我小時候每天必須面對的。我沒有空間成為我有機地學習成為的人,因為每當我表現出一點敏感時,我的父母就表現得好像他們知道該怎麼做。
我記得我小時候認為我的大多數表兄弟、叔叔和熟人都對我有攻擊性。 「男孩子不哭」。 「你看起來像個女孩」。 “你想成為一個小女孩嗎?”諸如此類的句子,多年來一直在我的腦海中迴響。他們讓我遠離了我的真實本質。
在成長過程中,虐待和痛苦一樣變得自然。這意味著,不管被抓到的後果如何,打扮得像個女孩,玩娃娃和化妝就成了我的身份。
我的父親於 1989 年被謀殺,當時我大約 7 歲。我為此自責,因為我以為我希望他也能這樣,這讓他的死所帶來的創傷更加嚴重。我母親被趕出家庭,因為她拒絕在我父親死後嫁給他最親近的表弟,這是傳統。從那一刻起,我是由女性撫養長大的:我的阿姨和祖母。
我以為父親的過世會讓我的生活好一點,但我錯了。因為我們社會的結構方式使女性也延續了她們自己面臨和忍受的有毒男性氣質。
由於對我應該受到的對待方式的分歧,我目睹了比我希望的更多的暴力,即使是在我的家庭內部。
在大多數社會中,「超級男子氣概」及其維持霸權的企圖已經讓一些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例如同性戀者、少數民族、移民、窮人和遭受勞動剝削的人。
我記得8歲時,我嘗試穿著姐姐的衣服走出家門,要求每個人都叫我保拉。我被一群男孩毆打了。我知道其中一些男孩秘密地喜歡它。但如果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被抓到任何這些行為,他們總是會遭到暴力。
在我的童年時期,安哥拉捲入了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安人運)和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安盟)之間的內戰,直到2002年4月簽署和平協議。的時候,1994年,我被送到西班牙的一所寄宿學校學習。
我的家人送我出國上學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知道,如果我不離開,我在安哥拉的生活將會變得非常困難,因為我的個性。我被送到西班牙聖奧古斯丁的一所神學院。在那裡我開始認為也許將我的一生奉獻給上帝對我來說是最好的選擇,並專注於學習神學。
快轉到今天,幾乎沒有什麼改變。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能夠要求平等權利的時代,網路帶來了橫向和橫向的現實感。然而,在許多非洲社會,這一現實並不包括 LGBTQIA+ 人群,作為同性戀者或僅僅是非二元性別者,可能會被判死刑。在這些情況下,宗教往往是主要的理由,人們相信並宣揚,死了比成為某種「性變態」更好。
2013 年,回到安哥拉,當我在 TEDx 羅安達演講時,我決定公開出櫃自己的同性戀身分。作為公眾視野中的一個人,這對我來說是邁出的一大步。演講結束後,很多人建議我離開這個國家,因為我處於危險之中。
我花了30多年的時間才找到戰鬥的力量,並將自己定位為故事的主題。在閱讀或聽到諸如「班圖人不是同性戀」、「同性戀是歐洲傳入的」或「違反上帝的律法」之類的事情時,我需要將自己奉獻給上帝並「在精神上」痊癒了」。我是一個令人憎惡的人。
我還與朋友和家人進行了真誠的交談,他們學會了接受我。然而,他們拒絕接受別人。我認定自己是同性戀已經 20 多年了,但有時我仍然必須自我約束,因為害怕被拒絕、被取消或精神上的枯竭。
我現在住在葡萄牙,在那裡我們開始定義種族主義及其結構,它如何主要影響來自非洲僑民的黑人,特別是來自前殖民地的黑人,以及它如何仍然是一個需要修復的開放性傷口。人們聚集在一起抗議對黑人的謀殺,例如被一名公開的種族主義者槍殺的演員布魯諾·坎德·馬克斯。
但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想知道為什麼人們仍然會在看到彩虹旗時轉向另一個方向,並說 LGBTQIA+ 在這場鬥爭中不受歡迎。
這使得我們重新思考如何教育年輕人變得更加迫切。我和一些教授發起了一份公開請願書,要求在葡萄牙引入一門名為「公民教育」的新學科,目的是確保我們的孩子了解性別平等、自我認同、反種族主義等知識。請願書需要 4,000 個簽名才有資格提交議會。該連結位於我的 Instagram 帳戶簡介中。
不斷地整理自己的碎片,並將自己的各個部分放入盒子中以避免受到虐待,這並不容易。酷兒在我們的集體想像中仍然沒有代表性。憑藉地位更容易對抗歧視。因此,如果我們必須佔據強調我們存在的空間,那麼這些空間就應該是我們創作的藝術。
這個制度是不正當的,但我們需要繼續爭取平等,特別是當我們是競技場中間的人。
保羅·努諾·德·阿澤維多·帕斯科阿爾出生於里斯本,在安哥拉長大。他是一名演員、舞者、模特兒、設計師、製片人和人道主義活動家,關注非洲社區。
____________
查看文章中表達的觀點僅代表作者的觀點。
您是在非洲工作的領域公認的專家嗎?您是非洲人後裔嗎?您想分享一個挑戰傳統男子氣概觀點的個人故事嗎?給我們發電子郵件:[email protected]
_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