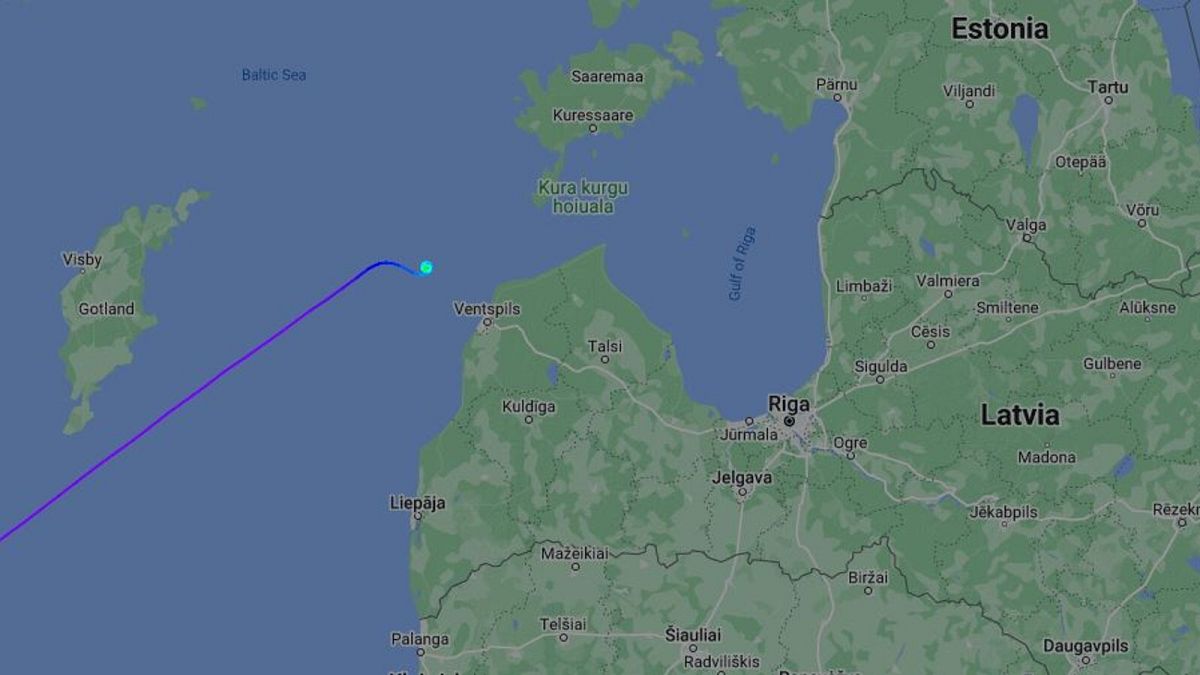圍繞烏克蘭東正教的狀況及其與克里姆林宮的聯繫的問題,使其從精神領域淪落到充滿惡意影響、宣傳和欺騙的激烈政治舞台,就像蘇聯時期一樣。
2022 年初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所引發的政治爭議在去年 8 月變得尤為突出,當時基輔頒布了一項法案,限制莫斯科宗主教區領導下的烏克蘭東正教的活動。
根據烏克蘭和西方安全部門的說法,東正教的這個分支——與烏克蘭獨立的東正教不同——一直與克里姆林宮和俄羅斯情報機構 FSB 有直接聯繫,* 維持著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密切合作。
索邦大學商學院風險主席、法國國家憲兵軍官學校研究員克里斯蒂娜·杜岡·克萊門特(Christine Dugoin-Clément) 表示:「歷史學家能夠查閱的檔案文件能夠證明這些聯繫,並且只涉及蘇聯時期。
然而,「(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在烏克蘭領土上擁有極其廣泛的網絡,可以直接從現場收集資訊。在戰爭期間,任何資訊都可能具有戰術軍事意義,並在後期具有戰略重要性。
烏克蘭東正教莫斯科宗主教區的數十名神父因收集軍事資訊並將其傳遞給俄羅斯軍事情報機構格魯烏而被烏克蘭法院定罪。
其中一些神父已與烏克蘭戰俘交換並被送往俄羅斯。
國家安全和宗教自由
烏克蘭關於在宗教事務上保護國家憲法的法案有一個明確且公開的目標:禁止莫斯科教會在烏克蘭的活動,因為它與克里姆林宮有聯繫,並支持其在鄰國的戰爭。
“鑑於俄羅斯東正教是侵略國政權的意識形態延續,是代表俄羅斯聯邦和‘俄羅斯世界’意識形態犯下的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幫兇,俄羅斯東正教的活動烏克蘭的東正教教堂是被禁止的,”法律規定。
這引起了一些外國基督教徒的擔憂,他們擔心這項法律可能為所有宗教自由樹立危險的先例。
烏克蘭政府最近在辯護中指出,不會對願意正式公開譴責俄羅斯入侵和克里姆林宮政權政策的烏克蘭莫斯科宗主教區信徒施加限制。
巴黎聖弗拉基米爾大帝的烏克蘭希臘天主教主教赫利布·隆奇納 (Hlib Lonchyna) 告訴歐洲新聞,烏克蘭的法案並未侵犯宗教自由。
「它的目的是保護我們的國家免受一個對我們發動戰爭的國家的侵害。該法案旨在打擊和禁止與戰爭直接相關的宗教組織、主教和神父在烏克蘭進行的(敵對)活動,」他說。
“其中一些人向敵人傳達烏克蘭軍隊的戰略地位和烏克蘭基礎設施的位置。”
梵蒂岡認為
受到東正教等拜占庭儀式的祝福,但在羅馬天主教教皇的領導下,烏克蘭的希臘天主教會實際上知道成為莫斯科的十字準線意味著什麼,以及自由的基輔為其信徒提供了什麼。
基督教信仰在利沃夫和烏克蘭西部部分地區有據點,於 1946 年在約瑟夫·史達林的統治下被正式鎮壓,其歷史教區的財產和場所被移交給莫斯科東正教教宗主教區。
1980年代末,希臘天主教神父和信徒從流亡歸來後,希臘天主教徒進行了改組,成為烏克蘭獨立的堅定支持者。
然而,對於教會來說,教宗方濟各對烏克蘭針對莫斯科宗主教區的禁令的批評,稱他“擔心祈禱者的自由”,也引起了強烈的共鳴。
然而,隆奇納主教仍然對教宗的擔憂持懷疑態度。
「羅馬(梵蒂岡)有一個非常強大的莫斯科遊說團體。教宗有很多顧問,」他解釋道。
他很快指出,事情並不是那麼黑白分明:他說,並非所有留在莫斯科宗主教區的烏克蘭東正教信徒都支持克里姆林宮。
「在烏克蘭軍隊服役的士兵中,有來自莫斯科宗主教區和基輔宗主教區的東正教信徒、希臘和羅馬天主教徒、新教徒,以及穆斯林和猶太人。他們都在為烏克蘭的獨立而忠誠地戰鬥,」隆奇納主教解釋道。
為什麼莫斯科認為它仍然應該在烏克蘭擁有發言權?
與全部受梵蒂岡統治的天主教徒不同,東正教基督徒可以要求其他東正教教會的獨立管轄權,即所謂的獨立。
當任何國家的東正教會,特別是新獨立的國家,要求伊斯坦布爾東正教大公宗主教區蓋章獨立(也稱為托莫斯)並得到其他獨立東正教的承認時,就會授予這種形式的獨立。 。
雅典大學神學家尼科斯·庫雷梅諾斯(Nikos Kouremenos)博士告訴歐洲新聞台:「根據十多個世紀前確立的普世原則,一個領土政治地位的變化應該帶來其教會地位的變化。 」
這項古老的原則在過去兩個世紀中大多數擁有大量東正教人口的獨立國家的誕生時都得到了應用。
這意味著直到 1991 年,在東正教世界看來,烏克蘭以及蘇聯其他地區都正式處於莫斯科宗主教的統治之下。
然而,當烏克蘭宣布獨立時,其教會獨立問題成為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與烏克蘭擺脫俄羅斯控制欲的鬥爭交織在一起。
同時,基輔對許多東部斯拉夫人來說具有重要的精神意義。
在俄羅斯和莫斯科存在之前,基輔羅斯是斯拉夫世界和東正教的中心,是第一個東斯拉夫國家,然後在十世紀基輔弗拉基米爾大公統治下皈依基督教。
基輔羅斯東正教信徒建造了許多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聖地,例如佩喬爾斯克修道院和聖索菲亞大教堂。
弗拉基米爾王子在切爾索尼索斯(Chersonesos)接受拜占庭牧師的洗禮,切爾索尼索斯是當時的希臘城市,靠近今天的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
隨著烏克蘭獨立的東正教在獨立後崛起,莫斯科宗主教區試圖在佩喬爾斯克修道院等地方發揮影響力並保持控制,特別是在 2014 年獨立廣場革命之後。
2022 年 3 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初期,烏克蘭安全機構 SBU 突襲了佩喬爾斯克修道院的地下墓穴,尋找親俄武器藏身處,其影響基輔事務的企圖得到了充分展示。
Tomos 和“Thermos”
在莫斯科宗主教公署顛覆基輔教會的過程中,經過近三十年的激烈談判,才從普世宗主教巴塞洛繆那裡得到了宣布其獨立的托莫斯。
2019 年 1 月主顯節當天,托莫斯在時任烏克蘭總統彼得·波羅申科 (Petro Poroshenko) 的注視下被交付給烏克蘭都主教埃皮法尼烏斯一世 (Epiphanius I)。
這位烏克蘭前國家元首誇口說,基輔教會的獨立是他個人外交上的成功。
波羅申科當時的政治對手弗拉基米爾·澤倫斯基嘲笑了托莫斯,稱其為“熱水瓶”,對波羅申科在激烈的總統競選活動中的教會熱情進行了猛烈抨擊。
然而,基輔的獨立地位只得到 15 個官方東正教會中的少數教會的認可:塞浦路斯、希臘和埃及亞歷山大。莫斯科仍將其視為「分裂組織」。
「在烏克蘭宗教問題上,東正教世界存在明顯的分歧,」庫雷莫斯解釋。
他補充說:“例如,一些可以被視為莫斯科衛星的東正教教堂,例如貝爾格萊德和安條克的塞爾維亞和敘利亞宗主教區,都公開拒絕了獨立的基輔東正教教堂的想法。”
「其他宗主教區,如喬治亞和羅馬尼亞的宗主教區,尚未採取任何正式步驟承認烏克蘭(東正教)教會。他們已經棄權了。
因此,許多烏克蘭東正教信徒一直猶豫是否離開莫斯科宗主教轄下的教會並加入獨立的烏克蘭東正教教會,擔心可能因分裂而被逐出教會。
然而,這本身就變成了分裂。
戰爭開始後,數千名烏克蘭人離開了莫斯科宗主教轄下的烏克蘭教會,加入基輔的自治教會,而許多其他人儘管是堅定的烏克蘭愛國者,但仍然是第一個教會的崇拜者。
烏克蘭大主教西里爾·霍沃倫解釋說,禁止莫斯科宗主教區在烏克蘭開展工作的法案也是一個實際的解決方案,可以鼓勵那些猶豫不決的人加入烏克蘭獨立教會,特別是在被佔領土。
「俄羅斯宗主教區在被佔領土和自由領土上都有自己的直接結構,」他告訴歐洲新聞。
「所有在莫斯科宗主教之下非正常(在佔領期間通過武力)接受的烏克蘭宗主教區教堂立即被列為非法。這是烏克蘭禁令最明顯和最重要的影響」。
至於烏克蘭控制領土上的俄羅斯教會,新法律在製裁他們之前無法避免更長的憲法程序。
「根據烏克蘭立法,教會不具有法人資格。只有社區才具有法人資格,」Archimandrite Hovorun 說。
「這些社區在臨時國家記錄中進行了登記。根據這種登記,他們享有一些特權,例如天然氣和電力的折扣價格,或者他們可以免費使用市政或國家財產」。
他說,證明宗教團體與宗主教區的隸屬關係可能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過程,必須經過法院直至歐洲人權法院」。
霍沃倫大主教在基輔的住所總結道:“即使事實證明,該社區的莫斯科附屬機構將受到最嚴厲的製裁,那就是被剝奪租賃公共財產建築物的權利。”
霍沃倫現在是瑞典一所內部正統大學學院聖伊格納蒂奧斯的普世主義和國際關係學者。
他是莫斯科宗主教區烏克蘭教會的成員。他曾與俄羅斯宗主教基里爾共事,但在目睹俄羅斯東正教對克里姆林宮擴張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持日益增加後被迫辭職。
霍沃倫被俄羅斯宗主教本人解除了聖職,作為一名學術研究員,他現在只對君士坦丁堡普世宗主教做出回應。
“俄羅斯世界”,傲慢與異端的結合
關於莫斯科宗主教區活動的烏克蘭法律明確指出了一個特定問題:「『俄羅斯世界』意識形態的危險」。
這一廣受關注的學說被視為俄羅斯國家及其代理人的藍圖,為政治行動提供文化和意識形態基礎,將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和其他東歐社區置於克里姆林宮的政治控制之下,無論是透過領土吞併或擴大俄羅斯勢力範圍。
現任莫斯科宗主教基里爾在講道中支持了這一教義,為俄羅斯對鄰國的軍事侵略和宗教宣傳辯護,這是透過援引基督教道德原則來粉飾和證明使用武力的事實上的方式。
來自各國的千餘名東正教神學家和學者強烈譴責「俄羅斯世界」的想法:
「我們拒絕『俄羅斯世界』異端邪說和俄羅斯政府對烏克蘭發動戰爭的可恥行為,這種行為源於這種卑鄙且站不住腳的教義,並得到了俄羅斯東正教的縱容,是極其非正統、非基督教的。
儘管沒有被徹底禁止,但大多數東正教教堂都受到蘇聯當局的密切監視,特別是在冷戰期間。
甚至西方的流亡宗教團體也被牧師作為臥底滲透。
普丁總統和基里爾宗主教之間的聯盟以「俄羅斯世界」的名義重新啟動了這些做法。
自冷戰以來,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塞洛繆與美國保持著極其友好的關係,而基里爾宗主教則積極利用教會的精神和教會作用來為俄羅斯的擴張主義辯護。
儘管如此,「沒有一個東正教教會譴責基里爾為異端,原因之一是民族主義問題幾乎植根於所有東正教教會,」庫雷莫斯博士解釋道。
「如果我們試圖指責基里爾是異教徒,因為他是民族主義者,我們不知道我們可以在哪裡停止,因為在其他教會,在羅馬尼亞,在格魯吉亞,在塞爾維亞,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民族主義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