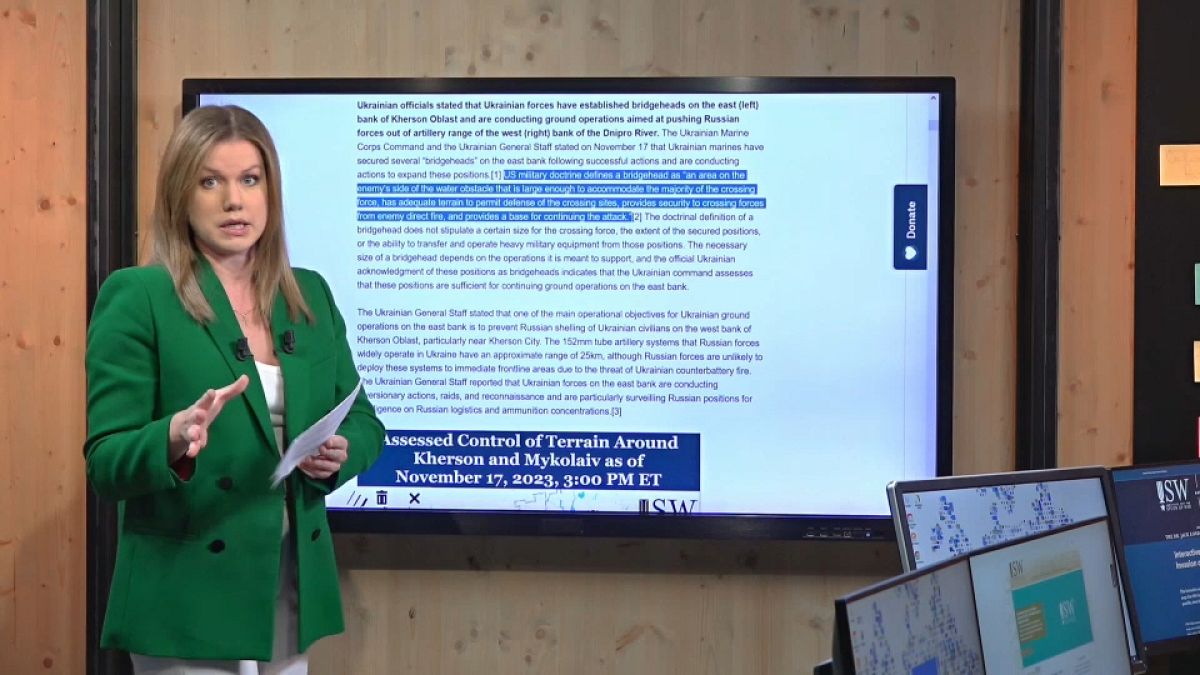蘇聯第八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統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去世引發了人們對當代世界歷史關鍵時期的重新反思。
在統治衰落的蘇聯期間,戈巴契夫因其在結束冷戰中所發揮的作用而被西方視為和平締造者,並因此於 1991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他發起的改革旨在實現國家現代化並拉近與歐洲其他國家的距離,最終導致蘇聯解體和 15 個主權國家的成立。
再加上歐洲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國家的民主化和獨立浪潮,戈巴契夫在歐洲大陸和世界的結構性轉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們回顧了蘇聯第八位也是最後一位領導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
隨著戈巴契夫在 1980 年代中期登上蘇聯最高權力,世界見證了世界上最大國家和最大核國家的權力描述方式發生了變化。
他的妻子賴莎·戈巴契娃(Raisa Gorbacheva) 在許多工作會議和公務旅行中的出現,讓人們得以罕見地了解這位蘇聯領導人的生活——與他的前任不同,戈爾巴喬夫公開並直言不諱地表示,她是他領導下的主要支柱。
然而,賴莎·戈爾巴喬娃不僅僅是《開放的第一夫人》:她積極促進婦女參政,並因其慈善工作而聞名,包括為兒童癌症治療籌集資金。
據說,1999年賴莎因白血病去世,享年67歲,戈巴契夫對此深感震驚。
戈巴契夫繼承了一個迫切需要經濟改革的國家,他尋求維護蘇聯的完整性,並為改造國家而奮鬥到底。他的主要政策體現在他舉世聞名的「三合一」:改革、開放和新政治思維。
他看到了一條透過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來加速經濟發展的方法,最初僅限於合作社和合資企業。同時,他避開了自上而下的統治,選擇更多地出現在人民之中,以拉近國家與公民的距離。
今天,西方許多人仍將戈巴契夫在國際舞台上的成就視為他的主要遺產——以他與美國同行(首先是羅納德·雷根)的會面為先鋒。
1985 年 11 月,這兩位爭執數十年的世界強國領導人在日內瓦舉行了首次面對面會晤,雷根和戈巴契夫隨後又舉行了四次年度高峰會。
這些高峰會是結束冷戰的第一步,啟動了國際緩和,其中包括削減戰略核武的協議,例如《中程核武條約》,該條約消除了一整類飛彈的存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和蘇聯集團領導人之間首次開始發展非正式關係。儘管一開始有所保留,最終裡根將蘇聯稱為“邪惡帝國”,但雷根和戈巴契夫發現他們的關係變得更加積極,有時甚至溫暖。
戈巴契夫從政壇退休後繼續與西方領導人會面,與雷根和老布希都保持著友好關係。親屬後面。
戈巴契夫希望國家開放並拉近與歐洲其他國家的距離,這不僅促使柏林圍牆倒塌,也促進了更密切的經濟聯繫的發展。
在英國,戈巴契夫的領導時代恰逢瑪格麗特柴契爾擔任首相,與雷根類似,大多數人預計兩人之間的關係即使不會升級為公開的敵意,也會冰冷。
然而,鐵娘子——一個蘇聯記者創造的綽號——在 1984 年說過一句名言:「我喜歡戈巴契夫先生。我們可以一起做生意”,勸阻裡根遠離敵對政治,並為美蘇關鍵峰會打開了大門。
1989年12月,戈巴契夫在梵蒂岡會見教宗保祿二世。這次會議是共產主義蘇聯與梵蒂岡之間外交關係的分水嶺,此前梵蒂岡曾陷入嚴重的敵對行動。
約翰·保羅二世原名卡羅爾·沃依提拉(Karol Wojtyla),他的波蘭背景意味著他對祖國和東歐其他地區共產主義的垮台有著既得利益,因為東方政策試圖在該地區重建天主教會的存在。
與拒絕與梵蒂岡會面並公開警告約翰·保羅二世不要干涉的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不同,戈巴契夫在 1989 年會見了教皇,並發誓要允許蘇聯有更大的宗教自由。
在喬治·H·W·布希擔任美國總統期間,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關於核裁減的談判進一步發展,最終於1991 年7 月簽署了第一個START-1 協議,隨後在後蘇聯時代簽署了START-2 和START-3 協議。
在戈巴契夫的所有旅行中,不可避免地會有他的私人翻譯帕維爾·帕拉日琴科(Pavel Palazhchenko)(如後圖所示)陪同,後者後來成為戈巴契夫基金會的負責人之一。
然而,戈巴契夫領導下的蘇聯並非一切都那麼美好。面對大規模失業、犯罪率飆升和其他負面趨勢,俄羅斯主導的蘇聯也必須應對其成員國慢慢變得不安並走向最終獨立的問題,特別是在波羅的海國家。
1991年1月,蘇聯軍隊在立陶宛發動暴力鎮壓,三天之內阻止其離開蘇聯,造成14人死亡、140人受傷,給戈巴契夫的和平主義者形象留下了永久的污點。
戈巴契夫對暴力升級的解釋是,使用武力的命令是駐立陶宛的蘇聯軍官下達的,莫斯科的反動「黑暗勢力」迫使他採取行動,儘管此前他避免了在波蘭和東德的暴力行為。
1991年8月,戈巴契夫在克里米亞的一棟政府別墅度假,此時莫斯科的強硬派試圖奪取政權,他們認為,這是為了保留蘇聯在其昔日的邊界,並恢復其昔日的輝煌。
策劃者派遣克格勃官員前往戈巴契夫的度假屋拘留他,但未能對新近當選的新改革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爾欽採取行動。
所謂「八人幫」政變遭到葉爾欽和莫斯科反共示威者的抵制,兩天後就宣告失敗。然而,蘇聯的命運已成定局,回到莫斯科的戈巴契夫距離永遠離開克里姆林宮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了。
1991年8月政變後,戈巴契夫面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領導階層的猛烈批評。
俄羅斯總統葉爾欽一直在推動全面禁止蘇聯共產黨。戈巴契夫不同意葉爾欽的觀點,他認為葉爾欽是民族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轉而推動政黨的更新。
最終,葉利欽獲勝。他關閉了共產黨,安排解散了聯盟,並要求戈巴契夫在 1991 年底前辭職並撤離克里姆林宮。
戈巴契夫卸任後依然活躍,並找到了新的目的,創立了戈巴契夫基金會。
該非營利組織的任務是研究改革的歷史以及俄羅斯和世界歷史的當前問題,而戈巴契夫則參與了許多慈善項目,並多次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演講。
為了紀念這位政治家的80 歲生日,2011 年在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舉辦了一場音樂會,邀請了世界上最知名的明星參加。之風》與英國政治家緊密相連。
戈巴契夫近年來批評俄羅斯正在發生的變化,並公開支持不同的聲音,包括他是該報聯合創始人的《新報》。
戈巴契夫和《新報》主編德米特里·穆拉托夫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相隔30年。
根據記者阿列克謝·韋內迪克托夫報道,俄羅斯開始軍事入侵烏克蘭後,戈巴契夫非常沮喪,並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丁「毀了他一生的事業」。
「戈巴契夫的所有改革——歸零、化為灰燼、化為煙霧,」他的密友維涅迪克托夫在七月說道。
事實上,戈巴契夫幾十年來一直批評普丁。在2007 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這位前蘇聯領導人深入探討了普京,表達了他對「種族間關係令人不安的發展以及政府並不總是及時做出反應的仇外心理和不容忍現象」的擔憂。
戈巴契夫唯一的另一個小插曲出現在2014 年,當時他表示,俄羅斯吞併的克里米亞是烏克蘭的一部分,“基於蘇聯法律,這意味著政黨法律,沒有詢問人民”,並表示他相信人民有權進行全民公投。
然而,專家認為,這一評論來自戈巴契夫晚年的需要,以使他的遺產更容易被普通俄羅斯人接受,他們大多認為他是曾經強大的蘇聯帝國解體的罪魁禍首,而不是作為一種方式普丁的和平。
身為俄羅斯和烏克蘭混血兒,戈巴契夫從來不相信普丁希望將基輔置於莫斯科控制之下並重新納入俄羅斯軌道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觀念——尤其是不是透過武力。
反過來,普丁對這位即將離任的蘇聯領導人表現出最低限度的尊重,由於“日程安排衝突”,他選擇不參加 9 月 3 日星期六的葬禮。
普丁出現在莫斯科中央臨床醫院舉行的開棺紀念活動上,並帶來鮮花,並在展出的戈巴契夫遺體旁短暫停留。
此外,普丁發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宮已決定戈巴契夫的葬禮將只具有「國葬的元素」。
根據遺囑,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將安葬在莫斯科新聖女公墓,與他的妻子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