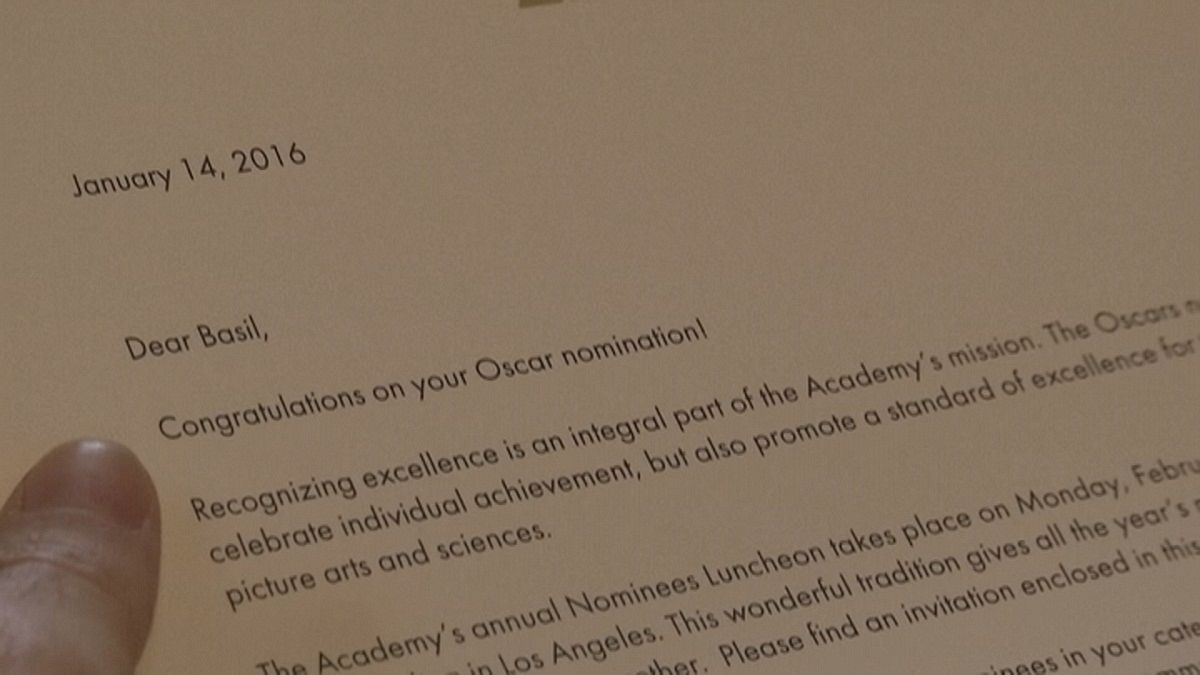上週末是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的兩週年紀念日。世界各地的許多人走上大城市的街頭來紀念這一天。在柏林,抗議活動是由總部位於德國的烏克蘭年輕人協會 Vitsche 組織的。該組織組織抗議、文化和教育集會,為難民提供支持,並協調對烏克蘭的人道主義努力,旨在擴大烏克蘭人在德國的聲音。
「vitsche」一詞在烏克蘭語中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烏克蘭社會的早期階段,大約六世紀。它指的是集體做出決策並制定變革以服務社區的理事會。這就是為什麼該組織選擇這個名稱作為他們的組織,並認識到它在烏克蘭遺產中的深刻意義。
在全面入侵之前,一行人就已經預感到了接下來的恐怖。他們的第一次抗議發生在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前一個月,當時邊境局勢緊張。當時,他們的抗議規模很小。今年,已有數千人參加了示威活動。
到現在兩年了,維切透過在社群媒體管道上提高意識並組織活動,每天都在處理戰爭問題。發言人 Krista-Marija Läbe 表示,他們不想讓人感覺或傳達出無能為力的感覺。 「情況比兩年前更加嚴重,但我們仍然可以做出重大改變。我們有辦法繼續支持烏克蘭,使其能夠贏得這場戰爭。因此,我們的每個成員都致力於確保人們了解如何幫助烏克蘭以及需要迅速採取行動。這給了我們巨大的力量,」她補充道。
輸掉這場戰爭可能意味著失去我們的國家認同
克里斯塔出生於烏克蘭,但在德國長大。儘管她本人很幸運,家人沒有傷亡,但她的一些家人不得不逃離烏克蘭。 「我擔心我的兩個小姪子;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現在 13 歲的長者可能會被徵召入伍。這場鬥爭不僅關係到人身安全,還關係到維護我們烏克蘭的身份和存在。 「輸掉這場戰爭可能意味著失去我們的國家認同。這是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的共同擔憂,他們擔心我們可能永遠無法返回烏克蘭。過去兩年,損失慘重,無數朋友、家人和同事面臨難以想像的損失。
毫無疑問,烏克蘭人希望繼續保衛自己的國家並解放被佔領土,因為別無選擇。 「另一個選擇是讓整個烏克蘭看起來像是被佔領的領土,」克里斯塔說。 「那裡沒有人權,沒有法治,兒童和平民被綁架,還有酷刑室——這些人沒有安全。”
還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據稱,兩年前戰爭爆發時,總統弗拉基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在被提議撤離後說道,「我需要彈藥,而不是搭車」。這句話至今仍然適用。烏克蘭目前正面臨彈藥短缺問題,導致阿夫迪夫卡等戰略要地撤離。但克里斯塔說,我們還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即使美國大選不符合我們的意願,我們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我們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持——武器、財政以及將俄羅斯資產轉移到烏克蘭。
克里斯塔補充說:「即使在國際法範圍內,也有很大的行動空間。我希望歐洲其他國家加強支持力度,因為我們的整個未來都處於危險之中,整個大陸的未來也處於危險之中。我們在前線也沒有足夠的彈藥,但烏克蘭人拒絕放棄。
戰爭已經抵達德國
克麗斯塔在柏林強調,儘管前線距離2,000多公里,戰火已蔓延至德國。 「這也是一場資訊戰,俄羅斯的假訊息多年來一直在這裡活躍。我們只是需要提高人們的認識,讓人們意識到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它的直接影響,」她說。自俄羅斯開始侵略烏克蘭以來,德國政府觀察到來自俄羅斯控制的媒體和外交管道的虛假訊息增加。據聯邦內政部稱,俄羅斯政府機構越來越多地利用各種管道操縱輿論,為其行為辯護並誹謗烏克蘭,同時將西方描繪成敵對國家。
迪米特里·安德羅索夫:我打電話給烏克蘭的朋友哭了
迪米特里·安德羅索夫 (Dimitri Androssov) 於 2022 年 5 月逃離俄羅斯,目前在德國聯邦議院工作。他因抗議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而在祖國遭受迫害。 2月24日對他來說尤其痛苦。 「那天晚上我一夜沒睡,」他說。 「來自烏克蘭的第一份報告是早上五點左右傳來的。普丁的那次演講……有種怪異的感覺。我打電話給烏克蘭的朋友,哭了。
不久之後,安德羅索夫在社群媒體上呼籲抗議戰爭。他盡快開始抗議,不久就被逮捕了。同年3月獲釋後,試圖從事反戰活動。 5月,他再次被捕,在派出所遭到毆打和掐脖子。此後,他離開了祖國。
他堅信,在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被擊敗之前,戰爭不會結束。他對歐洲新聞台表示:“西方應該大力支持烏克蘭,使其能夠獲得解放。”
儘管西方現在已經了解了俄羅斯總統普丁的真正意圖,但許多人仍然不清楚他的政權的性質。 「這些自稱為菁英的人,要不是來自前蘇聯共產黨,就是來自克格勃秘密警察,就像普丁本人一樣。這就是他們的心態、他們的思維方式、他們採用的方法、他們的願望, 「安德羅索夫說。
儘管如此,他仍然對俄羅斯的未來充滿希望。安德羅索夫說:“作為人民自由黨(PARNAS)的成員,我相信俄羅斯可以擁有美好、和平和自由的未來。” “不幸的是,有一些受過教育、聰明的人,他們目前沒有機會影響自己國家的事態發展。如果烏克蘭贏得戰爭,這些人就有機會返回俄羅斯,參與塑造我祖國的未來。”
這位訓練有素的政治學家、德國學者、德語教師與德國有著深厚的淵源;十年前,他在德國聯邦議院完成了實習。然而,戰爭的念頭從未離開過他:「德國是一個非常適合居住的地方,但是當你總是與受戰爭影響的人接觸時,他們的親戚、家人都在烏克蘭,那麼我相信,無論無論你身在世界何處——德國、非洲或美國——你都無法擺脫這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