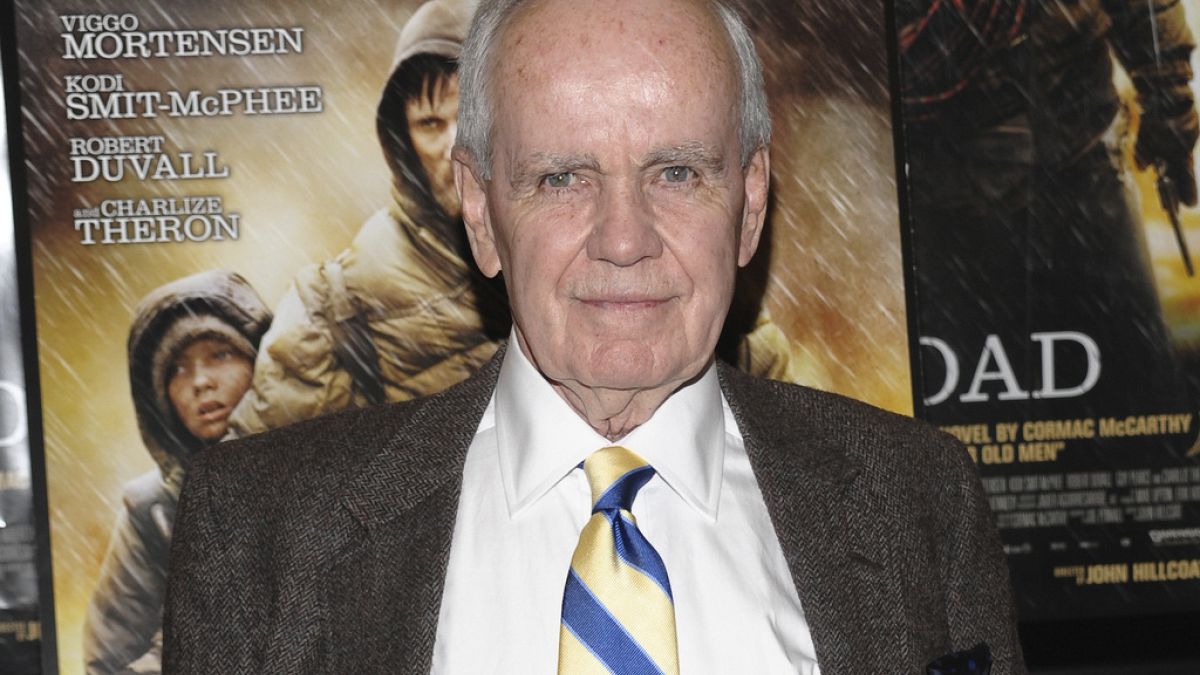1986年4月26日凌晨,當時的蘇聯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電廠的一個機組發生爆炸,引發的大火持續了9天,所造成的爭議和後果至今仍令人感受到。
由於原子工廠第四反應器的安全測試失敗,爆炸釋放了 5000 萬居里的輻射——相當於 500 枚廣島原子彈。攜帶放射性粒子的雲飄到了加拿大,隨後釋放出有毒的雨水。
4 月是這場災難發生 33 週年,自那以後,由於美國網絡 HBO 於 5 月和 6 月播出的一部描述災難後果的電視劇,該事件一直佔據頭條新聞。
廢棄工廠和鄰近的普里皮亞特(工廠大部分員工都住在這裡,如今已成為一座鬼城)的旅遊經營者報告稱,自節目播出以來,預訂量增加了 40%。
這場災難以及莫斯科的處理方式讓人們深刻地認識到蘇聯體制所籠罩的保密文化,對許多人來說,這標誌著一個結構的首次削弱,並將在五年後崩潰。
兩名工廠工人在設施內喪生——一名在爆炸中喪生,另一名在爆炸後立即因致命劑量的輻射而死亡。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28 名消防員和工廠員工死於急性輻射症候群 (ARS)。在最初因 ARS 住院的 134 人中,有 14 人在接下來的十年內死於輻射誘發的癌症。
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死於輻射相關疾病的最終死亡人數為 9,000 人,環保運動組織綠色和平組織估計為 9 萬人。
這事件仍是史上最嚴重的核電廠事故。
來自烏克蘭、俄羅斯、德國、波蘭、土耳其、伊朗和匈牙利的歐洲新聞記者在這裡分享了他們對當時的回憶。
Natalia Liubchenkova,烏克蘭基輔(當時的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距離切爾諾貝利 135 公里
娜塔莉亞在基輔出生長大,切爾諾貝利災難發生時她只有 18 個月大。事件發生後,她的父母在祖母的陪同下將她送到烏克蘭東部哈爾科夫市的家人朋友那裡,距離核電廠所在地 610 公里。
「顯然,我對那段實際災難的記憶並不多,但我的腦海裡確實有一段類似短片的東西。我記得當我們去鐵路時有一種恐慌感。」車站,並且知道我要去某個地方旅行。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在哈爾科夫度過。當我的父母發現切爾諾貝利的情況確實會影響我們時,他們就把我送到了那裡。那可能是事情發生幾週後的事了。我爸爸看到幼兒園正在疏散,就知道事情很嚴重。
「而且,當時有傳言說,政要高層要把孩子送走,機場裡也擠滿了孩子。有什麼事情瞞著,就算有再大的宣傳機器,也會傳出去的。」那是想向人們隱瞞它。
「在哈爾科夫,我學會了說這句話:『我的媽媽在哪裡?我媽媽在基輔。然後當我終於回到基輔的家時,我媽媽就在那裡,她問我,你媽媽在哪裡?我當面說我媽媽在基輔。這對我媽媽來說是一個艱難的時刻,因為顯然我不認識她。
「我想,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切爾諾貝利就在那裡,是自然的事情,直到我成年後,我才意識到它的規模。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從未正確地討論過它,我們從未正確地解釋過它是如何發生的或它如何影響人們。
“我們傾向於在歷史上塑造不同人物的英雄,但我不記得有人告訴我們那些應對災難的人的故事,即所謂的取消派,他們實際上冒著生命危險。”
奧琳娜‧柳布琴科娃 (Olena Liubchenkova),娜塔莉亞的母親
1986 年春天,22 歲的奧萊娜 (Olena) 是一名經濟學家,與丈夫和女兒住在基輔。儘管決定將女兒送離基輔,她說直到災難發生大約六個月後,她才意識到切爾諾貝利的危險和破壞的全部程度。
「我第一次聽說切爾諾貝利災難是當我的祖母打電話說她在教堂聽到核電站發生爆炸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不可能。我告訴祖母她有一個新的每週都有“世界末日”,我們在學校了解到核工業受到很好的監管。
「一兩天之內,我的鄰居告訴我,孩子們正在從普里皮亞特(距離工廠最近的城鎮,也是大部分勞動力的居住地)撤離,而且他們生病了。然後成年人也被疏散了。
「5月1日,有一年一度的慶祝活動。有一種節日氣氛,我記得天氣很暖和,5月1日這麼暖和——25度以上,這種情況並不常見。窗戶開著,每個人都在外面,這很有趣,沒有人想到切爾諾貝利。
「5月14日,我丈夫工作的製造廠所屬的幼兒園被疏散。就在那時,他奇蹟般地買到了火車票,而火車票是不可能買到的(因為想要離開的人太多),他帶納塔莉亞去哈爾科夫見她的祖母。
「我仍然沒有驚慌,我不明白[輻射]如何影響我們的健康。我只是非常難過,我一直在我身邊的小寶貝去了一個沒有我的地方。她會學會不用我說話,不用我拿著她的第一本小書。
米科拉‧烏薩蒂 (Mykola Usaty),娜塔莉亞的父親
災難發生時米科拉 27 歲,在工具製造廠擔任首席機械工程師。
「4 月26 日是一個非常美好、陽光明媚的日子。那是一個星期六,對我來說是一個工作日,我第一次聽說這起事故是當我站在工廠附近與同事交談時,有人說:'你知道,很多救護車都朝切爾諾貝利方向過去,可能是核電站發生了什麼事。
「我記得我們的工廠被要求製造這些巨大的金屬容器。很多。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們有必要的設備,因為這是一個工業工廠。事實證明,這些是裝滿了的容器用從直升機上扔到受損反應爐上的沙子來撲滅大火或遏制輻射。
「我們也被告知,我們必須用水清洗我們的廠房,我們正在盡可能地清洗它們,包括牆壁和地板。
「因為我們沒有訊息,所以有很多八卦和猜測。大概是在五月中旬左右,人們開始大規模離開這座城市,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每個人都試圖離開,或者至少是這樣把孩子們送走,因為工廠還在繼續運轉——基輔也照常運轉。
安東·赫梅爾諾夫 (Anton Khmelnov),莫斯科,俄羅斯(當時的蘇聯)—距離切爾諾貝利 853 公里
災難發生時安東 13 歲,住在當時的蘇聯首都莫斯科。他記得拿切爾諾貝利作為學生笑話,他的叔叔在事故現場周圍工作,但沒有說他到底在那裡做什麼。
「對我們來說,由於當時訊息傳播的方式,這個消息並沒有立即傳來。我們沒有互聯網,新聞一點一滴地傳來。但後來,隨著社會更加開放,我認為我們學到了更多。
「我們確實掌握了一些信息,因為我的一位叔叔因服兵役被派去做一些[與災難有關的]工作。我們並不真正知道這是什麼事情,它是在相對保密的情況下完成的。我們透過家人知道他的身體受到了一些影響,但他今天還活著,而且已經是一個相當老的人了。
「我們小時候,我們大多會拿發生的事情開玩笑。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曾經告訴我們,在酸雨中奔跑時要小心。但酸雨的故事自冷戰以來就一直存在。這是我們當時酸雨幽默中的另一句台詞。
「切爾諾貝利被認為是一場共同的災難,因為蘇聯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政府將全國各地的人們帶到切爾諾貝利[工作]。所以他們可能是烏克蘭人、俄羅斯人或來自其他共和國的人。我認為重要的是要說這是一種常見的痛苦。然後,在蘇聯解體後,它有點退縮到不斷擴大的邊界後面。現在已經是另一個國家了。這和在自己的國家發生災難已經不一樣了。
德國慕尼黑(當時的西德)西格麗德·烏爾里希 (Sigrid Ulrich) – 距離切爾諾貝利 1,800 公里
西格麗德·烏爾里希(Sigrid Ulrich)1986年住在慕尼黑,並擔任德國新聞社德意志通訊社(Deutsche Presse-Agentur)的記者,享年32歲。她記得面對延遲反應時的困惑,以及對食物污染的恐懼。
「我的主要記憶是混亂。因為我認為兩天都沒有任何資訊。蘇聯證實了這起事件,當時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進行的測試顯示,事件發生兩三天後某處發生了事件。在此期間,一股強風從東方吹來,席捲了切爾諾貝利以西的所有國家。後來他們才告訴我們,我們不應該出去,尤其是,我們不應該在雨中出去。
「我們感覺有點被遺棄了。有報道稱,報告一出,一些家庭就帶著孩子乘飛機前往加拿大或其他地方停留幾週,直到情況變得明朗為止。我的表弟告訴我她的一些朋友這樣做了。
「有很多蔬菜被丟掉了。今天仍然有來自這個地區的野豬,你不應該吃。問題之一是牛奶,以及如何處理它。它最終被存放在大約 200 節火車車廂中,因為它有毒。
「巴伐利亞州的一位環境部長在鏡頭前拿了一種白色液體,說喝牛奶沒有危險,然後他把一根手指放進去舔了舔。 20年後,他們告訴我們,他把一根手指放進去,但又舔了另一根手指。
「切爾諾貝利事件在某種程度上是 20 世紀的一個[標誌],就像登月旅行或甘迺迪被謀殺一樣。我女兒說,她認為這結束了伍德斯托克時代。她對我說,你很幸運,你有 20 年的“伍德斯托克幻想”,認為某些事情可能會在全球範圍內發生變化。一切都結束了,因為我們意識到人為災難可能無法控制。所以這是技術和氣候變遷整個麻煩的開始,對我來說這就是開始。
Sebastian Zimmermann,伊瑟隆,德國(當時的西德)—距切爾諾貝利 1,800 公里
切爾諾貝利災難發生時,塞巴斯蒂安四歲,與父母住在多特蒙德附近的伊謝爾隆市。他記得關於外出玩耍和一週不吃蔬菜的警告。
「當時我四歲,所以我對當時的情況沒有完整的[記憶],但我的父母告訴我不要在花園的沙箱裡玩,這非常重要,因為雨中充滿了放射性。我們應該不吃任何蘑菇,我認為第一周不吃任何蔬菜。
「他們沒有解釋,只是說玩沙子很危險,不健康,雖然只是一周,但你絕對不能這樣做。大約八、九歲的時候,我得到了更多關於原因的資訊。我意識到我沒有在沙盒中玩是件好事。
「我的父母很快就得到了消息。我父親是一名工程師,所以他對技術感興趣,所以他對此非常清楚。在其他一些國家,例如法國或東德,他們對此保密。我們有很好的資訊。這是眾所周知的,這不是秘密。我們從電視、廣播和報紙上獲得了資訊。
Thomas Siemienski,弗羅茨瓦夫,波蘭 – 距離切爾諾貝利 1,078 公里
1986 年春,托馬斯 29 歲,住在波蘭西部的弗羅茨瓦夫,在該市的大學擔任語言學研究員。雖然波蘭不是蘇聯的一部分,但其共產主義政府被視為蘇聯的「衛星國家」。
「首先,你應該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災難並沒有發生。至少不是正式的。但許多波蘭人都知道切爾諾貝利災難,因為他們正在收聽自由歐洲電台或美國之音等外國電台。所以我們知道正在發生一些事情,但不知道具體是什麼,但我們意識到周圍可能會有危險。但當沒有官方明確的訊息時,謠言、恐慌或奇怪行為就有很大的空間。
「我當時在工作的地方,看到一位女士拿著一小瓶碘。我們用它來消毒傷口。這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產品。這不是很令人愉快,因為當你在傷口上使用它時會灼傷。我看到這位女士拿著瓶子,我想好吧,她需要消毒一些東西。
「然後我看到她喝了它。這非常令人驚訝,也有點可怕,但有人解釋說,根據謠言,你必須喝碘,因為它可以保護你免受輻射的影響。 33 年過去了,我仍然不知道這是否屬實。
土耳其希萊 Zeki Saatci – 距離切爾諾貝利 1,445 公里
災難發生時,澤基只有八歲,住在伊斯坦堡附近的土耳其小鎮希萊,位於黑海西緣,與烏克蘭隔水相望。
「黑海地區以其茶葉和榛果生產而聞名。當時,公立學校向學生提供當地食品,尤其是榛果。我曾經很喜歡它們,它們仍然是我最喜歡的零食之一。我們的老師告訴我們「黑海的孩子之所以更聰明,是因為他們吃榛果」。我還沒有檢查這是否屬實,但這令人鼓舞。
「然而,在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人們對堅果是否受到輻射產生了疑問。有傳言說,因為已經曝光,所以不能賣到歐洲國家,所以才在國內免費發放。之後,我記得在學校課桌上看到了未吃完的榛子包。
土耳其迪茲傑 Tuba Altunkaya – 距離切爾諾貝利 1,460 公里
圖巴也來自土耳其黑海地區,事故發生時她才三歲。她也記得,事後,大人們擔心學校分發的堅果可能會導致癌症。
「大多數人認為榛果和茶葉受到高輻射,因為它們的田地靠近烏克蘭。有很多癌症病例,每當黑海地區的人失去親人時,我聽到他們說,這一切都是因為切爾諾貝利。
「全球癌症病例呈上升趨勢,而且由於診斷水平的提高,癌症病例數比20-30 年前還要高,所以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調查表明切爾諾貝利事故在癌症數據中所扮演的角色。
Behnam Masoumi,德黑蘭,伊朗 – 距離切爾諾貝利 3,100 公里
來自德黑蘭的貝納姆在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時才三歲。 1986年,伊朗與伊拉克交戰六年,食品採用優惠券制度配給,而農產品出口——包括該國青翠的里海地區生產的大米、水果和蔬菜——大幅下降。鑑於該國與俄羅斯(該國譴責了 HBO 的連續劇)及其有爭議的核計劃的強大聯盟,切爾諾貝利今天仍然是伊朗人爭論的話題。
「伊朗自1980年以來一直與伊拉克交戰。但切爾諾貝利災難兩年後,即1988年,當伊朗接受停火併在八年後恢復經濟時,有很多傳言稱阿拉伯國家不購買伊朗北部的石油。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當伊朗全面恢復布希爾核電廠的核子計畫以發電時,伊斯蘭共和國領導人選擇不與其最親密的盟友俄羅斯合作開展該項目,這表明他們對切爾諾貝利災難。他們邀請日本和德國公司與之合作,儘管一個月後兩家公司都退出了這個計畫。 1995年,也就是災難發生九年後,他們恢復了與俄羅斯的合作。
「今天,災難發生三十年後,當伊朗核計畫成為國家和伊朗人民最關心的問題時,人們不再擔心切爾諾貝利事件。 Twitter 在伊朗被禁止,但非常受歡迎,每個人都使用 VPN 來訪問它,在 HBO 劇集播出後,受歡迎的伊朗 Twitter 用戶抨擊該電視節目是美國的宣傳。
「然而,魯哈尼總統的重要顧問、多產的推特用戶赫薩梅丁·阿什納(Hesameddin Ashena)最近發布了一條有關HBO 劇集的推文,提出了一個問題:謊言的代價是什麼?
Attila Kert,佩奇,匈牙利 – 距離切爾諾貝利 1,375 公里
切爾諾貝利災難發生時,阿提拉 15 歲,住在蘇聯控制的匈牙利南部的佩奇,當時匈牙利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集團的一部分。
「我記得,爆炸發生幾天后,當我們聽到第一個消息時,學校裡一群即將參加醫學院入學考試的高年級學生穿著綠色醫生工作服進來了,在學校的院子裡用捲心菜製作了一個巨大的頭骨——由於擔心核污染,捲心菜在市場上以像徵性的1 福林(而不是通常的20-30 福林)出售。
「國家電台的新聞一直說輻射沒有顯著增加,沒有危險。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周里,他們會高興地談論輻射水平如何下降。我意識到這是共產黨宣傳的一部分。就像當一個孩子傷害了自己時,你試圖透過說「哦,沒什麼」來讓他們平靜下來。一小時後你會說,’哦,好多了’。